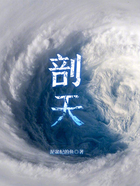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41章 那过去的事情(四)
张勇的故事停顿在这里,并排立在塘心的两个浮漂同时开始倒伏和跳动,跳动得很剧烈,一定是大鱼。但两人都没有收线提杆,只呆望着远方。
良久,张勇向陈相问出最为关心的问题,“林芳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过得很好。虽然一直只身一人,但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一直都是业务骨干,我离开后,首席的名头肯定就是她的了。大儿子在读大学,学校不错;小儿子刚升上高中,是一所寄宿制的省重点。最近两年她的气色越来越好,她熬过来了。”
陈相一五一十答着,眼前浮现出林芳的两幅模样,一个是光鲜靓丽的柔弱姑娘,一个是40多岁就有白头发的女强人。行走的时光吞噬一切,连一丝青春年华的倩影都不肯放过。两个个性天差地别毫不般配的人因为一个契机结合在一起,又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彻底走散,难以琢磨。
在张勇的描述里,林芳的决绝确实是难以理解的,陈相无从揣测,只能无限感慨生物本就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连鱼什么时候咬钩都参详不透,更无从参悟人心。
张勇听闻林芳的近况后,逐渐面露喜色。他终于注意到也包含喜讯的浮漂,开始手忙脚乱收线,却只收上来一个空钩。他不好意思地挠头笑笑,又抛出新的一杆,在等待的过程中把话题切到陈相身上。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张勇问。
“因为没钱途。”陈相闷闷地答。
“你都干五年了,才知道没钱途?早干嘛去了。”张勇面色疑惑,“我看你挺聪明的,跟赵栋梁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不至于到现在才觉察到这行不挣钱吧?”
“我打小就知道这不是个好行当,是赵栋梁逼我干这行的。”陈相一边说,一边把头扭向空旷的一侧,好让饵料碗消失在余光里。碗里成团蠕动的红虫像赵栋梁的脸一样,让他感到恶心。
张勇并不很意外,“这像是赵栋梁会干出的事。那人格外自恋,肯定觉得自己在哪个行当哪个行当就最好。”
“在你眼里,赵栋梁,是个什么样的人?”陈相顺着张勇的话问,“不用顾忌我,我不喜欢他。”
张勇沉吟一会儿,给出的答案也并不让陈相感到意外。
“他是台里我唯一看不起的人。性格扭曲,脾气古怪。你说他好强吧,工作多年一点成绩都没有;你说他是个怂包吧,他说起话来还怪硬气。业务能力不行,人际交往上还不开窍,但浑身散发一股莫名的优越感,谁都不服气。这种人啊,如果不是陈波带头哄着他,肯定早就被视为透明人了。”
“他和陈波关系很好吗?”陈相接着问。
张勇歪着脑袋思考了好一会儿,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这个不大好说。我刚去到台里的时候,他俩确实比较亲近,赵栋梁不搭理任何人,只和陈波讲话。但后来,不知道陈波怎么惹到他了,他连陈波都不搭理了,就只每天抱着本臭书躲到各种犄角旮旯看。
你可是想象不到他看的是什么书,易经,渔樵问对,都是一些给人算命用的东西。”
张勇叹出一口气,“这个人古怪极了,但也怪可怜的。他和陈波是同校同班,陈波专业第一,他吊车尾。来到台里后依然是吊车尾,连刚入职的实习生都比不过。但他特别勤奋,值完夜班不休息,再跟着梁老师值一个长白班。只要梁老师在,他必定在。
梁老师是资深预报员,也是个老烟鬼,一看天气图就要抽烟,呛得他直咳嗽。他也不躲,哪怕烟圈直冲脸上也要凑过去听梁老师的经验。
梁老师退休这事,对他打击特别大。渔樵问对就是那个时候被他摆桌子上的,还弄得特神秘,说什么谁摸他书让他报不准天气就跟谁没完,从此收获一个卖卦哥的外号。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可我看啊,赵栋梁比女人还难琢磨。”
张勇感慨完,偏头望了一眼陈相,只望到一个低垂的三分之一侧脸,连忙像是找补什么似的夸起赵栋梁来。
“赵栋梁虽然脾气古怪,但品性是很好的。刮台风那晚,临近你妈预产期。陈波估计是感觉到了什么,早早拜托赵栋梁上他家里去把你妈接到医院。那个时候气象台附近都是荒郊野岭,班车每天只有两趟,赵栋梁是骑着自行车回去的。
他把你们娘俩照顾得很好。台风过去的第三天,我到医院看望过你们,你妈刚渡过一劫睡得很沉,赵栋梁在一边给你喂奶换尿布。你又拉屎又吐奶浑身脏兮兮,熏得我都不想靠近,可赵栋梁一点不嫌弃,把你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看他守了几天夜挺疲惫的说找几个人轮流替他,他也不让,什么活儿都自己来不让别人沾手。他把你妈伺候得很好,一周以后就出院回家了。你妈回家之后,赵栋梁依旧守着她,给她煮红皮花生熬骨头汤,把气血养得很足。台里人轮流着隔三岔五去看望,都夸赵栋梁把她照顾得精细。
虽说我看不起赵栋梁,可这事他做得确实让人佩服。那阵子他和陈波不对付,但还是把陈波的嘱托落实到极致。陈波的死讯也是我们托他告知你妈的,你妈承受不了要寻短见也是被他劝好的,棘手的事全部被他一个人办好了。
这可能就是后来你妈乐意嫁给他的原因吧,他对待你妈真的是好到让人挑不出毛病。陈波在天之灵,一定很告慰。”
在张勇把赵栋梁的善行娓娓道来期间,陈相已把埋得很低头重新抬起,脸偏转回张勇那一侧,满是惊讶。
张勇瞥一眼陈相的面色,竟噗嗤一声笑了,“看来你对你后爸的误会不小啊。赵栋梁脾气太古怪,但心还是好的。就只是苦了你了,被他逼着入了个不喜欢的行业,被他耽误了。”
张勇说完,站起身伸了下拦腰,左右歪脖子,把脖子别得咔咔响,像是打群架之前的热身。他活动完筋骨又坐下来,把钓鱼椅调转方向,正对陈相坐着,两手交叉,显得很庄重。
“我们谈谈你的工作吧,我看了你的简历,你的目标是算法工程师,想搞人工智能?”
陈相点头,“但也不是非要做这个,只要薪资好看,有前景,我也可以去研究硬件,也可以去干销售。”
“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你就做算法,我公司刚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张勇神色得意,“你可别以为我的仪器全都是贱卖出去的,我只在湛江台亏,在其它地方挣得可不少。今年市场环境这么不好,我都还在盈利,靠得可不是成本低销路广,我们靠得是算法。”
陈相脸上的惊讶还未褪去,张勇为他耐心解释,“做气象仪器的厂不少,但大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都是买的标准进口件,自己组装,大家的成本大差不差,我们也不例外。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不论卖得再贵,客户都得认,因为他们没得选。
因为我们在仪器上添加了额外的功能,拿对流层多普勒激光雷达打个比方,标准款只能测出风向风速和液滴、气溶胶的粒径和数密度这种基础要素,但我们的仪器,还能给出边界层高度、云顶高度、光学厚度这种观测不到的东西。靠得正是算法。
我们研发基于观测量推演非观测量的算法,把算法集成在仪器上,直接为用户提供现成的产品,节省用户自行计算的精力。这是一个端到端的产品,仪器插上电调试好后就不再需要人操心任何事情,他们只需要在终端跟前等着配套软件自动画出美美的图。
所以实际上,我们卖的不是仪器,而是算法。”
“这可比纺织业、小商品出口什么的安稳多了。不用操心原材料、货源、进货价等等容易随市场波动的东西,只需要发挥这里的能力。”
张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人的智慧也好,机器的智能也罢,只要能依据海量数据,挖掘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并变现,财富自然会找上门。并且谁也抢不走你的东西,知识产权保护好,关注前沿与时俱进,这财富可以吃一辈子。
这是这个时代赐予我们的机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互联网行业趋于饱和正在走向谷底,但同样的技术拿到气象行业,仍旧是一片蓝海。”
和张勇一起畅想完未来之后,已是下午时分,鹅黄色的阳光打在半透明的PVC一体成型鱼桶上,折射出淡淡的虹彩。两人的桶里都挤满鱼,并且在一群灰不溜秋的脊背都掺有一抹亮眼的红。红罗非是鱼坑里的稀罕物,但两人都有幸钓上一条来。
陈相望着桶内那一方狭小的欢腾之地,内心无限感慨。都说人生是由一连串的惊喜组成的,他终于有幸体会到这一点。
当满怀希翼迎接白昼和黑夜,整个大自然都会来表示庆贺。在酝酿了五年之久的憧憬被现实一击而碎后,在准备彻底向生活妥协的第二天,他竟迎来了比预想的还要璀璨如意的希望。
他终于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涂抹特属于自己的图像,虽然他还是没有机会从线稿开始设计,但递到手中的现成线稿比他心中所期望的还要完美。
张勇支持他的所有想法,还要把他的初心——基于生成式模型的多源数据同化系统——作为公司的一条新的业务线,重点研发,重点推广。甚至赐予他最大限度的自由,打算直接为他注册一家子公司,让他独立管理和经营,就此把算法业务独立出去,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
对此,陈相既感激也不安。他呆在一个僵化的体制里整整五年,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但张勇却安慰他说虽然市场和天气一样瞬息万变,但也总有人能像老预报员那样凭借经验把天气预报做得比丢硬币要准。张勇已在其中摸爬滚打二十余年,将两代人的经验烂熟于心,对自己有自信,也对陈相有信心。
两人之间的这场命中注定般的相遇,自日中起,自日落结。在晚霞染红半边天时,张勇从两人的鱼桶中各挑出一条最大的鲫鱼,放到钓场提供的网兜中,剩余的全部倾倒回鱼坑。
向塘心奋力回游的鱼激起点点水花,把平静的水面变得波光粼粼。张勇始终注视着它们,直到游得最慢的那条红罗非一头扎向水底,扬起的粉红色晶莹剔透的尾鳍上闪现出转瞬即逝的光焰。
他收拾好渔具,把装有两条鲫鱼的网兜递给陈相,同时递出的还有一个黑色真皮搭扣小盒子。
盒子很精致,虽有岁月的痕迹但被保养得很好,皮子很亮,触感细腻,打开之后,里面立着一块手表。
这块万国牌追针计时表看起来就价值不菲,钢制外壳,宝石表盖,虽然周身布满划痕,但依旧在阳光下闪着奢侈品特有的柔光。这表像是有些年岁了,但表针依然在走动,走得顺滑安稳,显示的时间和当前时间相差不大,显然有在精心保养。
“这块表送给你,留个念想吧。”张勇站得离陈相很近,先前的兴奋已从脸上全然褪去,换回讲述往事时的那副忧郁样子,“这是陈波离世的那晚,从我手里借走的。这是块好表,是我最喜欢的一块,我一直带在身边,连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想过把它贱卖掉。”
张勇始终低头看捧在陈相手中的手表,以格外惋惜的口吻说,“陈波救下几万人的命,唯独没救下自己的。那晚他死得实在是蹊跷,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赶到南桥河边,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淹死在南桥河里。”
这句话说完后,张勇沉默很久,直到最后一丝霞光消隐在地平线后,近夜的天空被余晖染成粉蓝色,他才抬起头,注视陈相,眼里全是费解。
“我的这块手表,全名万国牌追针计时表,能实现追针、三问和万年历等最复杂的功能,磁化钛金属双针,前盖是蓝宝石玻璃,表壳是316L精钢,大师级设计,防水三米。它是名副其实的匠心制造,质量好到陈波被从入海口附近打捞上岸时,它还在安稳地走针。
陈波死在南桥河里,南桥河不是一条小河,不是一个旱鸭子能应付得了的。
可陈波不是一个旱鸭子,他水性极好,好到在海边救过落水儿童,好到每年端午都带队赛龙舟每年都拿区冠军,好到能从吴阳老闸口附近的宽阔江面上一口气游到对岸。别说三米了,就是把他绑着手扔到水深32米的湖光湖也能扑腾半天都不沉。
他的尸体上没有多少外伤,没有被憋在落水货车里,没有被重物撞击,更没有被杂物缠住卡住,他没理由被淹死。
除非,是他自己想死。”
余晖落尽,两人无言对视,目光都比无月之夜的天空还要晦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