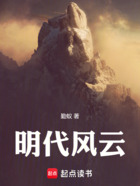
第31章 景泰帝的布置
乾清宫西暖阁,阳光微微斜,洒在雕花窗棂上,泛出一笼金色的光晕。
景泰帝端坐在紫檀木圈椅上,自今日早朝散会以来,他已连续处理政务近三个时辰。
他素来以勤政著称,此刻虽显疲态,腰背却仍挺得笔直,丝毫不减天家威仪。
景泰帝合上最后一本奏折——这是通政司转呈上来的今日内阁未决奏本……第二十四份。
他微微后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难得地舒展了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肩背。
“现下是几时了?”景泰帝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在空旷的暖阁内显得格外清晰。
由于司礼监掌握着常规政务的批红任务,随着太子返回东宫,掌印太监兴安也被景泰帝遣回了司礼监。
此刻随侍在侧的,是司礼监随堂太监舒良。
“回陛下,未时三刻了。”舒良疾步上前,将拧好的热毛巾呈上时,袖口绣的云蟒纹一丝不乱。
“王文、王诚二位大人已在廊下候了半个时辰。”他特意补充的细节,显露出宦官特有的机敏。
毕竟能让皇帝午后召见的臣子,必是极受信重的。
景泰帝闻言一怔,早朝后他确实传过这两位,不料被黄河决堤等事务耽搁。
正常来讲,能呈到他案头的事情,没有哪件事是小事。
今日通政司呈送的事务比往日多了一些,所以牵扯了景泰帝不少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最后也没想起来这两人。
想到此处,他严肃的眉间不禁掠过一丝愧色:“快宣!”
热毛巾敷面的片刻,他闻到淡淡的龙涎香——这是舒良的巧思,总是预先在毛巾中捂个香囊。
待擦拭完双手,景泰帝方才的倦意已消了大半,他顺手便将毛巾交还给舒良。
“臣等叩见陛下!“
踏入西暖阁的二人虽同为“王“姓,却是截然不同的气象。
都察院都御史王文身着绯袍,补子上威风凛凛的獬豸彰显着监察之权。
御马监太监、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王诚则着葵花胸背团领衫,腰间牙牌随着跪拜轻响。
前者是北直隶保定府的进士出身,后者乃凤阳府净身入宫的宦官。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却在景泰帝最艰难的易储之议时,不约而同地呈上了“乞早建元良(早点换太子)”的奏本。
“你俩无需多礼!”景泰帝难得地勾起唇角,连眼角都带了些许不符合年纪的细纹。
“谢陛下!”这两人不知圣上突然召见适合意图,便垂手立在御前,静待景泰帝发话。
只见景泰帝缓缓转过身,语气沉凝:
“朕自承大统以来,内忧外患交迫,来不及整饬吏治,一下竟耽搁至今。
如今瓦剌虽退,国用仍艰。
可六部九卿之中,却有蠹虫借机贪渎、结党营私!”
说到这,他指了指方才御案上垒成一堆的奏折。
“这半月来,通政司递上的弹章比去年多了一倍——山西粮道亏空、漕运衙门克扣粮饷……连科道言官都敢互相包庇!”
听到这,王文眉头一皱,躬身进言道:
“陛下明鉴。陛下明鉴。按祖制,京察本当在巳、亥年举行。今年虽非京察之年,但《大明会典》确有'特旨察典'的先例。若为整肃朝纲,确可权宜行事......”
王文说得确实有道理,自永乐以来,京察已渐成规制,每六年一次,在农历巳、亥年举行。
但景泰帝继位时正值多事之秋——1449年(农历的己巳年),瓦剌大军压境。
当年上半年,明英宗虽已启动京察,却因仓促亲征而中断,最终酿成土木堡之祸。
待景泰帝临危受命,既要抵御外敌,又要稳定朝局,自然无暇顾及京察之事。
所以景泰元年至今,确实未曾举行过正式的京察大典。
“权宜行事?朕看是有人巴不得朕拘泥成法!”景泰帝突然冷笑一声,打断了王文的奏对。
他的目光又扫向一旁的王诚,继续说道:
“东厂近日密报,说吏部考功司有人私改官员评语,甚至连南京留守太监都牵涉其中……王诚,你来说!”
王诚听到这,赶紧疾步上前,低声道:
“奴才正欲禀报,不止吏部如此。
东厂还发现,兵部武选司郎中赵纶,上月暗中宴请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七人,席间竟以‘土木旧臣’自诩,言语间多怨望之意……”
他一边说,一边偷偷看着景泰帝神色。
果然景泰帝听不得此言,他眼中寒光一闪,:
“好个‘土木旧臣’!朕待他们如何?他们心中难道没数?”
只见他越说越气,突然提高声调说道:“王文,三日后朝会,你便以‘整饬吏治、清查亏空’为由,奏请提前开启京察。
朕会命司礼监批红,都察院与东厂协同办理——六品以下官员,由你主持考核。五品以上……”
景泰帝目光转向王诚:“由东厂另具密档。”
王文心中一凛,拱手领旨道:
“臣遵旨。若是各部质疑期限……”
景泰帝闭上眼睛,默不作声,他显然知道肯定会有人拿这事来做文章。
只见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猛然睁眼,厉声说道: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瓦剌入侵之时他们怎么不说期限?”
说罢从案上抽出一本册子,丢给王诚:
“这是先前锦衣卫暗查的山西布政使司账目,虽说按例不在京察之列,但三日后不妨先拿此事立威。
至于那些‘念旧主’的……”
他意味深长地在此停顿,不再说下去了。
王诚会意,叩首领旨道:“奴才明白。
厂卫早已备好三百份‘密访名单’,凡与南宫有书信往来者,皆在甄别之列。”
景泰帝微微颌首,慢慢踱至紫檀木圈椅前,转身拂袖坐下,继续下令道:
“拟旨——加派御马监四卫营最精锐的士兵,东、西华门各增两哨兵马,南宫...”
他喉结微动,生硬将“太上皇”三字咽下,“南宫外围的守卫,按三班轮值,每班不得少于三百人,配齐火器。”
显然今日早些时候,太子朱齐的提醒仍然在这位帝王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他当时嘴上说着何惧宵小,但还是提防了一手。
“还有,”想到太子今日小心翼翼的样子,景泰帝冷声继续道:“东宫四周也增派一百精锐,加强巡逻值守!
上述兵马,三日内俱应调度到位,不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