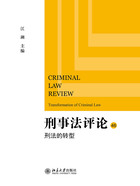
二、新型安全格局的轮廓
从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的视角,我们都能观察到有着显著预防目的的新型安全法的演变:因受上述力量驱使,在重要领域里,传统刑法正在由事后惩罚的惩罚性工具向着事前预防危险的预防性工具转变;同时,它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融合,在新型安全格局中形成一种新型的普通“安全法”,而这种新格局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垄断性的刑法及其保障措施主导。
(一)预防性刑法的加强
1. 实体法
在实体刑法中,预防性法律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对于公共产品和(诸如金融市场的)制度不断加强的保护上,以及对于各种危险活动的犯罪化上。犯罪化方面的例子包括:新增关于制造不受控制的客观危险情形的危险犯,新增关于在主观上预谋犯罪的危险犯(尤其是未完成犯和预备犯),新增关于犯罪合作的危险犯(尤其是合谋犯;由主观因素支配的合谋犯在普通法法系属于典型情形,而具有强烈客观特征的合谋犯则流行于欧洲大陆)。1
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危险犯将刑法上应受谴责的过错从结果的不法(所谓“结果犯”)转变为行为本身的不法(所谓“行为犯”)。目前正以极快速度扩张的“预备犯”( preparatory offences)这一类型则将刑事责任前移至预谋犯罪的预备阶段。在这里,犯罪的客观要素被主观要素取代。不同于其他危险犯类型的是,预备犯不是将刑事责任建立在实施某一行为所固有的风险之上;相反,刑事责任主要取决于(潜在)行为人的犯罪意图。于是,预备犯赖以建立的基础也就等同于未遂犯刑事责任的基础,但是它们又进一步延伸,甚至包括了(在时间上)处于“未遂” ( attempt)阶段着手实施的纯粹预备活动。2
在现行恐怖主义刑法中,这种发展趋势尤其明显,因为它就体现在对于——带有最终犯罪意图的——早期的(通常为日常的)准备活动的犯罪化中。该趋势的例证包括:将为参加恐怖主义培训而企图“离开国家”的行为,以及为支持恐怖主义犯罪而“筹集”资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3鉴于联合国( UN)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 FATF)规定的国际要求,德国于2015年将以上活动规定为犯罪。这些犯罪的客观要件通常只是由社会上可接受的行为构成。4由于这些条款中的最高刑罚偏高,预防性刑法的功能正在发展为类似于“保安监督” ( Sicherungsverwahrung)的功能。保安监督适用于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是被用于打击性犯罪或暴力犯罪。然而,与保安监督相反,上述新增的“前期阶段” ( preliminary stages)犯罪却不以前科为要件。5
2. 程序法
这一预防概念也给刑事诉讼法带来严重后果。由于实体法范围的扩大,刑事诉讼法如今也可适用于前期阶段,因而也许可调查新增的前期犯罪( preliminary stage of-fences) 。起源于情报法领域的秘密调查方法,被用于早期( early stage)调查,以便认定行为符合了——主导实体刑法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长期以来,这些调查方法已在刑事诉讼和行政执法中得到广泛运用,并且正在被进一步推广。最近的例证表明,除了电信监控以及对于住宅进行的室外监控( visual monitoring)和室内监听( eaves-dropping)外,德国现在已将“在线搜查” ( Online-Untersuchung)和“源数据监控” ( Quell-daten Überwachung)这样的调查工具纳入《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这些措施使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能够基于对犯罪清单中某个犯罪的怀疑,秘密侵入并搜查计算机系统。6在许多国家,这些新型调查措施改变了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对于民主秩序而言至关重要的——平衡,尤其是将平衡的天平倒向了安全一方。
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免予起诉和诉辩交易的权力也使得刑法更加灵活。因此,揭示真相和施加(惩罚性)报应的目的正在失去其重要性,而以目的为导向的结案策略(例如为企业施加一种建立合规计划的义务)可能会居于显要位置。7
(二)刑法之外安全制度的扩大
在刑法的上述发展的同时,预防性犯罪控制范围的扩大,以及从刑法向其他安全法措施的转变,都在刑法之外以多种形式出现:施加“巨额罚款”的行政刑法;警察法与其他行政法规;定点制裁;情报法;武装冲突法;民法;私人规范体系(比如合规规则)。与刑法相比,这些形式的规范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被用来控制犯罪的非刑事法律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容许较之传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更为广泛和更具弹性的权利侵犯。8
以上这些措施将在下文予以分析。就目前所知,这种分析在此前的学术文献中不曾有过。9为了分析之目的,本文将这些措施分为六类:①《德国刑法典》中传统的矫正与保安处分;②介于镇压与预防之间的行政处罚;③为了避免危险的措施;④秘密获取与使用信息的特殊制度;⑤应对例外情况的特殊制度;⑥私人规范体系和其他公私合作关系。此外,还有⑦以上主要类型的组合措施。
1. 传统刑法中的预防性保安措施:关注保安监督
正如在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德国的保安监督在形式上是《德国刑法典》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以来被认定为一种矫正与保安处分。它的适用前提是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然而,保安监督实质上属于(旨在避险的)预防法。10作出是否施加保安监督的决定,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因有严重犯罪倾向而对公共安全构成危险。不过,即使发现有此危险,也必须以犯罪前科为前提。
虽然德国近年来对保安监督进行了修改,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将其扩大用于预防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或者经济犯罪。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人,尤其是对尚未犯过任何罪的人,进行犯罪预测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也无法预料。另一方面,实行保安监督的前提是,通过刑事诉讼确定了先前犯罪的存在。由此,这种程序不仅提供了刑法上的基本保障,而且其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还具有“迟延的”效应。比如,将其用来对付恐怖主义初犯(尤其是自杀式袭击者)是不合适的。如此一来,保安监督迄今未被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现代复杂犯罪。相反,它已被上述预防性的前期阶段犯罪取代,而后者容许进行迅速审前羁押和判处长期监禁(人们对此提出的质疑是:这也有可能是对适用保安监督的规避)。
其他许多国家缺乏这样的措施。那么,这些国家只需考虑暴力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持续危险,而将这种考虑纳入传统刑法中的长期监禁刑的量刑决定。只不过,施加长期监禁刑通常也要以行为人实施过严重犯罪为前提。11
2. 介于镇压与预防之间的行政处罚:行政违法、行政处罚和没收程序
同保安监督一样,行政处罚和没收程序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们在法律实践中相当重要。
(1) “行政刑法”( administrative criminal law)的现代形式“违反秩序法” (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早在19世纪就在德国发展起来了。根据主流观点,它与核心刑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实际上并不属于刑法,也就不再与“道德上的谴责”联系在一起。12它没有规定监禁刑,大多数情况下的制裁只是行政法意义上的罚款,而这种制裁是不被载入“联邦中央登记册” ( Bundeszentralregister)的。
在诉讼法意义上,行政刑法与刑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一审判决是由一个(通常是更紧密协作的和更专业化的)行政机构作出,而且该机构也负责调查和起诉。如果当事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法院审理就会随之发生。法院审理大体上是要受到适用于常规刑事审判的规则的支配,但是某些程序性权利(特别是请求取证的权利)和刑事诉讼原则(特别是直接原则和口头原则)的适用受到限制。13
然而,与正在推广的欧盟“行政处罚法” (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law)类似,行政刑法不再仅仅作为打击轻微犯罪的有效工具使用,如今也被负责管理经济的专门机构用于执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构可能根据反限制竞争法的规定施加极高的行政罚款。鉴于这些行政罚款的严厉性,人们必然要问:在轻微犯罪案件中尚且存在一定的宪法保障,而在这些新型的大额行政违法案件中适用低于犯罪标准的宪法保障,是否具有正当性?14
(2)欧盟的行政处罚法在许多方面与德国的行政刑法相似。尤其在竞争法、银行监管法和(最新制定的)数据保护法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和美国司法部( DoJ)实行的数额可达数十亿美元的制裁为样板的行政罚款正在朝着不断增加的趋势发展。在欧盟的行政处罚法中,以下因素可以使行政程序的施行更加“奏效”:此类金融制裁在欧盟行政处罚法中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法律上授予执行部门以较大的权力范围和宽松的裁量幅度;刑事侦查机关被整合并入行政系统;以及(特别是)对于适用司法审查的事项作了限制性规定,而且减少了刑法上的保障措施。但是,就宪法或人权保障水平而言,这些程序一般会低于刑法。15
(3)在许多国家,犯罪所得或者——更广义地说——任何“无法解释的财富”是在新型没收制度的名义下被没收的。这些都被设计并标榜为预防性措施(比如在意大利)或民事诉讼手段(比如在美国)。因其在法律上被归类为非刑事处罚措施,故而用于确定犯罪资产来源的证据标准不如刑法中的高标准那么严格(例如,在美国只要求具有“证据优势”即可)。此外(与不得自证其罪的刑法原则相左的是),在确定可疑资产来源时,被调查者有合作义务。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程序规则,民事意义上的资产没收和用于对付“无法解释的财富”的类似手段,要比相应的刑事诉讼程序更容易实施。然而,这些程序规则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16
3. 避险法:聚焦普通警察法和外国人法
许多国家已经以所谓“避险法” ( Gefahrenabwehrrecht),特别是“警察法” ( Polizeir-echt)的形式,出台了旨在控制犯罪的措施。近年来,这些制度得以广泛适用。
(1)说到“警察法”,我们需要了解(镇压性或惩罚性)刑法和(预防性)警察法之间的基本区别。前者是与过去的犯罪行为相联系,而后者旨在预防未来的侵害。当警方根据警察法执法时,他们在职务上就不再是检察官的下属,也不再受相应的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其他国家没有制定这种自治性的警察法,它们是利用刑法追究预备行为,以达到避免即将发生的犯罪的目的(例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国家形成了独立的制度,比如英格兰的“控制令” ( control orders),其部分功能实质上等同于欧洲大陆的警察法。
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预防性干预在德国的——以警察法为基础的——“避险法”中甚至扩展到了更早的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抽象危险,德国的警察法只允许采取侵犯性较小的措施,特别是带有收集信息目的的措施。警察法规定,只有发生具体的危险,方可采取更具侵犯性(特别是侵犯人身自由)的措施。如今,随着《德国联邦刑警局法》 ( BKAG )和2018年《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 BayPAG)的立法改革,“紧迫的”危险已经足以表明对公民自由权利的重大侵犯是正当的。172018年《德国联邦刑警局法》规定了对于信息技术系统的秘密侵入,也规定了电子定位监控,这些措施也以类似的方式扩展到了防范恐怖袭击的早期阶段。18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BVerfG)也在采取类似的措施。在秘密监视措施方面,该法院在认定存在具体危险的标准时进行了扩张解释;它较少着眼于具体危险事件的发生,而更多着眼于行为人的危险性。19
同时,为达到预防目的而采取的警察法措施更多地造成了类似处罚的法律后果。在德国,这些措施包括新引入的“控制制裁” ( control sanctions),主要有:限制令;禁止进入或离开特定区域的命令;定期到警察局报到的义务;由警方对潜在危险分子发出的警告( Gefährderansprachen);以及针对惯犯采取的“控制网络”措施。20在2018年之前,德国警察法曾经规定,仅在全面披露作出决定的理由后方可实行短期的预防性羁押。21上述2018年《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也越过了这条界线,据其规定,在达到一定程度的危险时,可在获得法官许可令后处以长达3个月的羁押22,而且该羁押每次最多可延长3个月。23这样,在预防的理念下,预防性警察法越来越具备传统刑法的法律后果。这样,不仅可以按照《德国刑法典》以刑事判决或保安监督的形式,而且可以以纯粹预防性的警方羁押的形式实行预防性羁押。这种具有长期性的警方羁押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以传统刑法为基础的保安监督的范围,特别是前者不以犯罪前科为前提。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也有类似于刑法的严厉的“恐怖主义预防措施”24,这些措施不仅允许发布“禁止入境令”( exclusion orders),而且还允许实施“软禁” ( house arrest) 。这些“控制令”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只要怀疑一项活动具有恐怖主义动机,便可授予行政部门预测结果的广泛自由。适用于此类措施的程序性保障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其允许自由使用未经披露的情报信息。一项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是,英国《 2001年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第23条规定的对外国公民的长期行政拘留。欧洲人权法院(ECtHR)宣布该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 ECHR) 。25《以色列紧急权力(拘留)法》也规定了长期预防性羁押,而该措施是以严重克减的程序性权利和难以知悉的情报信息为基础的。26
(2)除了作为避险基本法的警察法之外,还有针对特定领域避险的特别法,比如食品法或核能法。在当前情况下,外国人法和移民法尤为重要。在这些领域里,对于外国人适用驱逐出境不仅是刑事定罪的结果(附有相应的保障措施),而且在无罪判决的情况下,它也可基于特别行政法——而不是刑法——中有关风险情形的规定而发生。27例如,根据《德国居留法》,当“事实使人有理由相信”外国人支持恐怖组织时,就已经可以考虑将其驱逐出境了。28在普通警察法领域,我们正在见证干预权力向着前期阶段的移动。同其他法律制度相比,证据标准和预测危害结果的标准都被降低了。
4. 秘密获取信息的特别制度:情报法、洗钱调查、数据收集的特殊方法
具备刑事制裁、强制权力、保护措施、行政处罚和避险措施等手段,旨在进行犯罪控制的“行政”系统正在越来越多地由信息获取系统加以补充。信息获取系统追求自身的目标,但同时(至少也)通过为犯罪控制提供信息来支持上述“行政”系统。
(1)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情报法也规定了监视和调查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并不以(刑法措施所要求的)犯罪嫌疑为前提,也不以(警察法措施所要求的)发生紧迫危险为前提,亦不以法院许可令为前提。这些监视手段被用于特别的目的(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用于控制犯罪。在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可以出于控制犯罪的目的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联邦情报局还被额外授权采取行动以获取涉及外国的特定形式的有组织犯罪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毒品交易、制假、洗钱或将外国人偷运入境的信息。29而且,德国16个联邦州的宪法保护局还要承担监视一般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附加任务。30随后,它们将收集到的信息部分地转给法院系统,供其使用,或者在联合机构(比如“联合反恐中心”)进行分析。在有的国家,同一家机构(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有权起诉犯罪,也有权从事情报工作。31向刑事司法和其他“行政”系统披露信息,这不仅发生在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政府机构之间,而且还发生在诸如联合反恐中心等联合数据中心。此类联合数据中心,汇集了来自众多控制系统的数据,以供共同使用。
(2)全球联网的反洗钱系统,是与情报系统相类似的、在体制上独立的信息获取系统。这些反洗钱系统规定了经由专门“金融调查组” ( FIUs)进行的金融数据分析,而此类调查机构又是紧密配合的国际网络的组成部分。正如对电信数据进行的分析一样,反洗钱机构是通过有义务合作的私人团体获取信息的。将来随着公私合作的扩大,这一措施有望变得更加有效。在此情况下,法院许可令也就没有必要了。就像情报部门一样,金融调查组的主要权力是收集信息;除了禁止某些金融交易的权力,它们通常也没有执行职能。相反,当其他控制系统的机构(比如检察与警察部门)共享分析机构的分析成果时,便会采取行政措施。检察与警察部门这样的控制系统基于自身干预权力采取行动时,便会用到以上信息。就有效性而言,促进金融数据分析专业化和外包,其益处在于能够让高度专业化的权威机构参与进来。不仅如此,它还允许在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这一点也与情报法类似),而且分析结果还要与刑事司法系统分享。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此类分析本来就是不被许可的。这样,金融行动组作为数据收集者,起到了预防和镇压(惩罚)的双重作用。
(3)就像预防洗钱一样,在电信数据领域,海量数据的收集主要是由私营实体进行的。虽然允许政府机构访问相关数据,但是当电信数据由众多不同的电信运营商以分散方式存储时,分析和筛查数据对国家来说就更加困难。有鉴于此,情报部门本身也大规模地存储电信数据,而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项目尤其证实了这一点。
(4)从个人的海量数据中收集信息,这不仅对于(由金融调查组收集的)金融数据和(由情报部门和警方收集的)电信数据具有重要性,而且还会涉及个人的位置与旅行数据。相关的分析系统在这一领域也正得以扩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乘客信息单元” ( Passenger Information Units,简称 PIUs )存储航空乘客数据( Passenger Name Records,简称PNRs) 。此外,特别是在反恐领域,根据欧盟理事会2007年《关于“第二代申根信息系统”的决议》 ( SIS II)第36条第2、3款和第37条,边检机构可以发出相应的警报。32警报机制造成的结果是,在所有边境检查或其他身份查验场合,当事人都要被登记,并统一由一个欧洲网络予以通报。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都有可能将定位与旅行资料的利用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5)还有一些松散型网络把来自不同机构的特殊信息汇集到联合数据库,而德国的反恐数据库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数据库储存的信息就包括具有潜在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联系人的信息。许多部门参与了这一数据库,其中就包括联邦刑警局、联邦警察局、各州刑警局、联邦宪法保护局、军事反间谍局、各州宪法保护局以及联邦情报局。尽管如此,鉴于法律上的规定和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无论是可以被存储数据的人群,还是可以被存储数据的范围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33
(6)总之,关于以上信息获取系统(联合数据库)可以总结如下:与纯粹基于刑法而进行的信息收集相比,这种方式跟通过情报部门、警察机构与私营实体进行的电信数据收集,以及通过金融调查组进行的金融数据收集一样,为安全机构提供了一些好处,它允许在没有嫌疑的情况下对人员进行筛查、进行风险分析,因而规避了刑法对于嫌疑程度的要求;而且,它还允许非正式的国际协作。然而,这也意味着许多公民被视为“预备嫌疑人” ( pre-suspects) 、“嫌疑人” ( suspects) 、“潜在风险” ( potential risks)或潜在“危险分子” ( endangerers) 。共享来自这些不同系统的数据,并由具有预防、惩罚职能的机构加以利用,这涉及在监控与分析上的一种特殊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就使用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而言。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5. 针对例外情况的特殊制度:紧急状态法、定点制裁、武装冲突法和过渡性司法
对于特殊情况,还有特殊的犯罪控制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允许严重偏离上述制度的“规范”。
(1)对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领域,有的国家制定了例外与紧急状态法。这些法律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宪法标准限制,尤其是因为它们中止了某些保障措施并为行政部门增设了权力。并且,它们还可以新增含义广泛的罪名条款,扩大现有的——以危险状况为前提的——干预权范围,或者降低根据刑事诉讼法采取措施所必需的嫌疑级别。34各个国家的紧急权力各不相同。例如在德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权仅限于确保国家的行动能力;而在其他国家,对于《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意义上“公共紧急状态” ( public emergency)期间的特定人权保护标准进行降低,这才是立法讨论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这导致了——旨在进行犯罪控制的——影响深远的干预权力的走向。例如,在禁毒战争中,哥伦比亚制定了一个例外法律,该法甚至规定了对毒品种植园和加工厂进行空中轰炸之类的军事行动。虽然这条规定不再是有效的法律,但在实践中它仍然被适用。
此类制度往往有意识地远远偏离现有的法律框架。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由扩大行政权的欲望所驱使;但是,这也可能是由不想通过权力的极端扩张而“玷污”一般法律的愿望所驱使。这样,例外法不一定被视为对宪法标准的忽视,也可以被视为试图规避对一般法律原则的永久性弱化。
法国为镇压与预防之间的嬗变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从2015年到2017年,法国通过设立紧急状态法的立法权(该项权力被延续了6次)以便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例如,法律允许政府在未经司法许可的情况下实施搜查和软禁。35在紧急状态下,“司法警察”措施被分配给“行政警察” 。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刑法上的保护条款不再适用,而且省长(或大区区长)和内政部长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行政法院代替了普通法院,从而可对“行政警察”采取的措施进行事后审查。与此同时,例外立法权已经让位于《法国加强国内安全与反恐斗争法》,而根据该法,普通的刑法和警察法中被塞进了许多此类非常规的措施。该例子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之间的边界被模糊了,而司法警察制度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所维护的是权力分立原则。
土耳其于2016年至2018年间颁布的含有预防性和惩罚性规范的紧急法令,也彰显了通过紧急立法对自由造成的极端侵犯。在刑法中,这些法令创设了国事罪,而这些罪名基本上涵盖了与葛兰运动(Gülen Movement)以及其他“威胁国家安全”团体相关的各种形式的行为。36违反这些规定的法律后果包括:从就业岗位解雇,将公司、高校、托拉斯企业等解散和国有化。37这些紧急法令是由总统主持的部长会议颁布的。38宪法法院无权审查它们,其他法律救济手段也几乎是不存在的。39此外,相关的程序性保障也受到削弱。40
(2)紧急状态法规定了从司法机关向执行机关移交权力,我们也可以在联合国和欧盟的所谓“列名程序” ( listing procedures)中观察到这一点。在这种程序中,嫌疑组织或人员的恐怖主义性质不是由法院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的,而是由国际委员会根据其设立的模糊标准并通过有宪法瑕疵的程序确定的。正如在紧急状态法中,个人权利受保护的程度严重不符合其国内程序所遵循的宪法标准。41该措施被归类为外交与安全政策,而不是国内安全事务。就联合国而言,此类措施的正当性依据在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而这项规定属于国际法范畴。
行政机构和国际组织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尤其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反恐制裁中。例如,根据安理会关于打击“伊斯兰国” ( ISIL)和“基地组织” ( Al-Qaida)的第1267、1989和2253号决议,立法部门、行政部门(由安理会成员组成的制裁委员会充任)和司法部门(由监察员充任)均由联合国安理会自己充当。这样,就不存在权力的分立了。除了对所有资产进行的预防性“冻结”,以及对于旅行施加的限制外,“列名”还会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其中包括“援助禁令” ( Bereitstellungsverbote),而该措施是指禁止向被列名人员或企业提供任何类型的援助。根据各国的相关刑法规定,违反上述援助禁令者也将受到惩罚。就其法律后果的性质而言,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行政处罚的范畴。诸如援助禁令这样的措施被称作“巧制裁” ( smart sanctions)或“定点制裁” ( tar-geted sanctions),这是因为,与传统制裁相比,它们不会影响整个国家,而只会影响某些个人或组织。
列名决定往往是在受影响人没有实质性参与权的情况下根据情报部门的信息作出的。受影响人只能在列名之后采取行动,以设法除名或申请不予执行。就联合国制裁而言,救济程序需要经过监察员(监察员提出的除名建议可由安理会成员一致决定予以拒绝);就欧盟制裁而言,救济程序需要经过欧洲法院( ECJ) 。然而,无论是联合国监察员还是欧洲法院,都不得充分审查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42
(3)特别是在“禁毒战争”“打击有组织犯罪战争”“打击网络犯罪战争”和“反恐战争”中,武装冲突法被用于与犯罪进行“斗争”,就其(法律)后果而言,它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和以色列对武装冲突法进行解释后,允许对恐怖分子进行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 。鉴于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个别国家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特别解释后而采取的这种做法,使得以打击犯罪为目的的国家杀戮成为可能。而且,与死刑不同的是,这种做法不需要符合刑法标准的证据,也不需要法官在个案中签发许可令。当国家对武装冲突法适用的对象的解释不限于战士( fighters)和参战者(combatants),而是扩展至新设类别的“非法参战者” ( illegal combatants)时,“斗争”理念便得以进一步扩张。实际上,这些“非法参战者”已被剥夺了所有的法律保护。由于对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的这种令人怀疑的解释,“战争”与“和平”之间,以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之间的传统类型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43通过武装冲突法进行的这种控制犯罪的形式,只起到预防的作用。
(4)在过渡性司法( transitional justice)或冲突后司法( post-conflict justice)情形下,我们还可以看到程序法的灵活性和预防性。在不法政体转变为坚持法治的民主国家后,会出现所谓的过渡性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过渡性社会中的刑法独具特色,它们可以对严重犯罪的行为人进行镇压性的惩罚。然而,它们通常也追求和解、和平以及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等预防性目标。为了实现和解与和平,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于被刑事起诉,而免于起诉的决定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7条规定的罪责原则和国际补充原则的范围内。当政府无法安抚某个(例如农村的)地区或无法对个别团体(例如前军事人员或有组织犯罪团体)行使其权力时,尤其如此。44这种有条件放弃刑事起诉的做法,往往是因为犯罪者数量众多,要是每一项罪行都起诉的话,就会完全超越国际和国内刑事司法系统的承受能力。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不同的(刑法)法律机制和准法律机制往往是相辅相成的。45这并不关乎从镇压到预防的转变。然而,过渡性司法表明,以确立个人刑事责任为核心的刑法体系只是过渡性司法整体模式及其目标的一部分。经常遇到的有条件地放弃刑事起诉、减刑、赦免、准许假释,通过真相委员会解决冲突以及其他办法,都在表明,在控制犯罪领域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目标。找出真相,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便是其中的两个目标,而此类目标超越了传统刑法的作用范围。46
6. 私人规范体系:合规制度和公私合作
用以推动犯罪控制的不仅仅是国家法规。特别是在遏制经济犯罪方面,新的私人规范体系和私营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私人合规计划不仅采用预防措施来预防犯罪,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也触发了私人调查。这些调查不受明确规定的法定保障措施的限制,并在实践中得到雇员以及(视情况而定)公司本身的默许,因为这些公司也害怕招致更严厉的制裁。这种私人调查是在未经相互法律协助程序的情况下“跨国”进行的,比如其可由美国的咨询或法务公司承担,甚至是发生在德国(比如在美国当局受理的西门子公司案中),而且该调查结果还要提供给法院。47这样的一些制度不是通过法律义务施加于人的,而是(更间接地)通过奖励制度得以实现的。对于实施了经济犯罪的某个公司而言,如果它当初设立了相应的合规计划,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充分配合当局,即便这样做是有损于其雇员的,那么它也有可能被赦免或者宽大处理。
(2)私营部门也越来越多地以公私合作的形式与其他国家控制系统相配合。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上述关于信息获取的法律制度中,比如涉及情报法、洗钱调查和人员定位的规定。如今,电信公司、银行、其他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比如律师、公证员和珠宝商)、航空公司和某些危险品生产商都有义务收集、汇总和向国家传输各种各样的数据。关于打击犯罪活动的尽职调查义务( due diligence duties)现在也扩大到对供应商和供应链的审查上。48这种“预防性犯罪控制的私有化”尤其导致了宪法权利的适用性难题。宪法权利原本是作为防止国家的侵犯而设置的,但是如今它们被认为是用来防范私营实体的。
7. 法律制度的结合与冲突
上述法律制度的结合也产生了额外的协同效应。在一个法律制度下收集的数据要与另一个法律制度下的职能机构进行交换时,抑或在不同的参与机构开展联合行动时,尤其如此。49在特殊情况下,不同法律体系的结合也会导致进一步的累积效应( cumulative effects),也就是更加严重的侵犯性,以及不同制度之基本原则之间发生的冲突(比如在警察法中基于风险的干预权,与受到刑罚威胁的前期阶段预备行为,二者发生结合时) 。50这种不同法律制度的结合也会导致较大的冲突。比如,由情报机构通过数据挖掘方式收集到的秘密信息被转发给刑事司法系统(该系统是不允许通过数据挖掘方式确认犯罪嫌疑的),并且将被用于刑事审判(而在审判中,此类证据一般是必须与被告人共享的)。对不同法律制度进行的个别考察和整体考察都清楚地表明,从传统的惩罚性刑法向新型的预防性控制战略的转变,正在侵蚀重要的公民自由。
1 关于此类犯罪的体系化和合法化,特别是涉及法律政策方面的论述,参见 Ulrich Sieber, Legitimation und Grenzen von Gefährdungsdelikten im Vorfeld terroristischer Gewalt, NStZ 2009, S. 353-364 ( 357-361)。
2 关于综述性介绍,参见前注〔6〕;关于基本原理,也可参见 Günther Jakobs, Kriminalisierung im Vorfeld einer Rechtsgutsverletzung, ZStW 97 (1985), S. 751-785; Johannes Kaspa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Grun-drechtsschutz im Präventionsstrafrecht, Nomos Verlag, 2014; 关于美国刑法,参见 Lennart Hügel, Straf-barkeit der Anschlagsfinanzierung durch terroristische Einzeltäter und deren Unterstützer, Duncker &Humblot, 2014; 关于英国刑法,参见 Sarah Herbert, Grenzen des Strafrechts bei der Terrorismusgesetzge-bung, Duncker & Humblot, 2014。
3 Vgl. Ulrich Sieber/Benjamin Vogel (fn. 4), S. 68-192.
4 参见 Ulrich Sieber (fn. 6). S. 353-364 (375-361); 以及Ulrich Sieber/Benjamin Vogel (fn. 4), S. 137-152。
5 关于保安监督的总结与法律比较,参见以下主编作品中的论文:Hans-Georg Koch (Hrsg. ), Wegsper-ren?: Freiheitsentziehende Maßnahmen gegen gefährliche, strafrechtlich verantwortliche (Rückfall-)Tät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Duncker & Humblot, 2011.
6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a条和第100b条。
7 参见本书中的文章 Emmanouil Billis & Nandor Knust Alternative Types of Procedure and the Formal Limits of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pects of Social Legitimacy p. 39 也可参见Emmanouil Billis Die Rolle des Richters in adversatorischen und im inquisitorischen Beweisverfahren Duncker & Humblot 2015 S. 106-110 S. 134-137。
8 See Ulrich Sieber Blurring the Categories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Law of War—Efforts and Effects in the Pur-sui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in S. Manacorda & A. Nieto eds. Criminal Law Between War and Peace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2009 pp. 35-69 63-69 .
9 关于这些措施的首次概述,Vgl. Ulrich Sieber Der Paradigmenwechsel vom Strafrecht zum Sicherheitsrecht Zur neuen Sicherheitsarchitektur der globalen Risikopesellschaft in K. Tiedemann/U. Sieber/H. Satzger u. a. Hrsg. Die Verfassung moderner Strafrechtspflege Nomos Verlag 2016 S. 351 ff.
10 例如,可参见 Jens Peglau Sicherungsverwahrung im Umbruch in T. Fischer/K. Bernsmann Hrsg. Festschrift für Ruth Rissing-van Saan De Gruyter 2011 S. 437-451 443 关于法律比较 参见 Hans-Georg Koch Gesamtschau in Hans-Georg Koch Hrsg. fn. 10 S. 494-543。
11 关于保安监督不被适用的情形,参见Ulrich Sieber fn. 6 S. 353-364 356 关于保安监督中的问题 参见 Georg Freund Gefahren und Gefährlichkeiten im Straf- und Maßregelrecht GA 2010 S. 193-210 Hans-Georg Koch fn. 15 S. 498-512 Helmut Satzger Sicherungsverwahrung - Europarechtliche Vorgaben und Grundgesetz StV 2013 S. 243-249 Heinz Schöch Sicherungsverwahrung im Übergang Neue Kriminalpolitik 2/2012 S. 47-54。
12 Vgl. BVerfGE 22 49 ff. Ulrich Sieber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Law in Germany in Matthew Dyson & Ben-jamin Vogel eds. The Limits of Criminal Law Intersentia 2018 p. 301 311 et seqq. .
13 例如,法院在拒绝采信证据方面拥有更广泛的权力,而驳回的理由可以基于《德国违反秩序法》(OWiG)第77条第2、3款。在违反秩序法程序中,取证也不遵守《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StPO)第244条的严格规定。而且(例如)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77条与第77a条对于取证的范围和方式规定了一些简便方式。
14 Vgl. Ulrich Sieber (fn. 17), S. 301 (326 et seqq. ).
15 Vgl. Gerhard Dannecker Der Grundrechtsschutz im Kartell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im Lichte der neueren Rechtsprechung des EuGH NZKart 2015 S. 25-30.
16 See Jon Petter Rui & Ulrich Sieber eds. Non-Conviction-Based Confiscation in Europ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n Rules Enabling Confiscation without a Criminal Conviction Duncker & Humblot 2015 pp. 245-304 265-275 .
17 参见 2018年5月18日《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第11条第3款。
18 参见2018年5月25日《德国联邦刑警局法》第49条第1款第2句序号2,以及第56条第1款。
19 参见BVerfG 141, 220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16年4月20日之判决,文书号:1 BvR 966/09,“联邦刑警局法判决”), Rn. 112。
20 Vgl. Michael Jasch Neue Sanktionspraktiken im präventiven Sicherheitsrecht Kritische Justiz 3/2014 S. 237-248.
21 关于德国的情况,可参见《德国联邦警察法》第39条(最多4天);《德国联邦刑警局法》第20p条结合《德国联邦警察法》第42条(最多4天);《巴符州警察法》第28条(最多2周);《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第17条(最多两周);《柏林一般安全与秩序法》第30、33条(最多4天)。
22 实施羁押的门槛是,“为防止即将发生或继续发生的对公众具有重大影响的违反秩序行为,或为防止犯罪行为,而不得已者”。参见《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第17条第1款序号2。
23 参见《巴伐利亚州警察职责法》第16—20条。
24 参见英国《2011年恐怖主义预防和调查措施法》 ( Terrorism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ct 2011); 关于此前的规则(所谓“控制令”),参见 Susanne Forster Freiheitsbeschränkungen für mutmaßliche Terroristen Duncker & Humblot 2010。
25 参见 House of Lords A and other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4 UKHL 56 ECtHR-A.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3455/05 19 February 2009。
26 关于以色列,参见 Elad Gil & Mordechai Kremnitzer A Reexam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a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2011 https //en. idi. org. il/publications/6707。
27 有关《德国居留法》中的驱逐权,参见以下文献的概述部分:Raimund Brühl Das Ausweisungsrecht in Stu-dium und Praxis JuS 2016 S. 23-29。
28 参见《德国居留法》第54条第1款序号2。
29 参见《德国联邦宪法保护法》第3条第1款;《信件、邮件与电信秘密法》第5条第1款。
30 比如,可参见《巴伐利亚州宪法保护法》第1条第1款第2句、第3款,以及第3条第1款序号5;关于萨克森州,参见萨克森州宪法法院2005年7月21日代号为 Vf. 67-I1-04的判决。关于基础性介绍,参见Eckart Werthebach/Brernadette Droste-Lehnen Der Verfassungsschutz – ein unverzichtbares Instrument der streitbaren Demokratie DÖV 1992 S. 514-522。
31 关于法律上的比较,参见 Xenia Lang Geheimdienstinformationen im deut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Straf-prozess Duncker & Humblot 2013; 关于《美国对外情报监视法》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书中的文章: Ste-phen Thaman The US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and the Erosion of Privacy Protection p. 217。
32 参见本书中的文章: Niovi Vavoula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hip in the'Security Union' The Case of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p. 307。
33 Vgl. BVerfG, NJW 2013, 1499 ff.
34 与此相区别的是所谓“必要性”(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4条规定的“小紧急避险”),这意味着允许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创制程序上的干预权力,即所谓的“拯救酷刑” (Rettungsfolter)。在德国刑法界,这一方法遭到广泛的拒绝。参见 Gang Wang, Die strafrechtlichen Rechtfertigung der Rettungsfolter, Duncker& Humblot, 2014。
35 这里的法国法是指 LOI n° 2015-1501 du 20 novembre 2015 prorogeant l'application de la loi n° 55-385 du 3 avril 1955 relative à l'état d'urgence et renforçant l'efficacité de ses dispositions。 该法的效力也同时得到了延期。
36 根据具有法律效力的第667号令(2016年7月23日)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这些措施影响到那些“长期以来与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FETÖ/PDY)有联系或有接触的自然人和实体”。
37 参见第667号令、第668号令(2016年7月27日)、第670号令(2016年8月17日)和第676号令(2016年10月29日),以及议会法第6749号( 2016年10月29日)、第6755号( 2016年11月24日)和第6758号(2016年11月24日)。
38 参见《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121条第3款。
39 Vgl. Metin Günday OHAL ihraç KHK' leri ve Hukuki Durum m Ankara Barosu Dergisi 2017/1 S. 29-38.
40 Vgl. Mehmet Arslan. Die türkische Strafprozessordnung Duncker & Humblot 2017 S. 9 ff.
41 Vgl. ECJ GC Judgment of 18 July 2013 Kadi II - C-584/10 - paras. 136 ff.
42 参见 Julia Macke UN-Sicherheitsrat und Strafrecht Duncker & Humblot 2010 Iain Cameron eds. EU Sanctions Law and Policy Issues Concern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Intersentia 2013 Matej Avbelj Filippo Fontanelli & Giuseppe Martinico eds. Kadi on Trial A Multifaceted Analysis of the Kadi Trial Routledge 2014 另参见本书中的文章Florian Jessberger & Nils Andrzejewski It is Not a Crime to Be on the List but ...- Targeted Sanctions and the Criminal Law p. 192 Nikolaos Theodorakis Legitimacy Effectiveness and Alternative Nature of Sanctioning Procedures in the UN Sanctions Committees and within the EU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 283。
43 关于武装冲突法和(在武装冲突之外)定点清除的有关问题, See Orna Ben-Naftali & Karen R. Michaeli We Must Not Make a Scarecrow of the Law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Israeli Policy of Targeted Killings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6 2003 p. 290 David Kretzmer Targeted Killing of Suspected Terrorists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or Legitimate Means of Def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2005 pp. 201-212 Nils Melzer Targeted Kill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rl-Wendelin Neubert Der Einsatz tödlicher Waffengewalt durch die deutsche auswärtige Gewalt Duncker& Humblot 2016 Marco Sassôli The Status of Persons Held in Guantánamo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2 2004 p. 100 et seqq. Ulrich Sieber fn. 13 S. 35-89 S. 36-37 S. 55-69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2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08 et seqq.
44 正如在哥伦比亚发生的情况那样,参见本书中的文章: John Vervaele Transi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 Co-lombia and Complementarity Policy unde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 140。以卢旺达为例,该国在处理种族灭绝案件时,也使用了减刑模式,参见 Nandor Knust Strafrecht und Gacaca Duncker & Humblot 2013 S. 262 254-257 284-289。
45 Vgl. Nandor Knust (fn. 49).
46 参见本书中的文章: Philipp Ambach Reparation Proceeding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A Means to Repair or Recipe for Disappointment p. 109 Jame Stewart The Imposition of Penal Sanctions at the Level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Other Forms of Justice Delivery p. 132 John Ver-vaele Transi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n Colombia and Complementarity Policy unde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 140。
47 参见 Marc Engelhart Sanktionierung von Unternehmen und Compliance 2. Aufl. Duncker & Humblot 2012 Ulrich Sieber & Marc Engelhart Compliance Progra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conomic Crimes Duncker & Hum-blot 2014 Ulrich Sieber Hrsg. Strafrecht und Wirtschaftsstrafrecht Dogmatik Rechtsvergleich Rechtstat-sachen. Festschrift für Klaus Tiedemann zum 70. Geburtstag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8 S. 449-484。
48 Vgl. Ulrich Sieber/Benjamin Vogel fn. 4 S. 49-67 S. 123-131.
49 参见 BVerfGE 133, 277 (2013年4月24日之判决,文书号:l BvR 1215/07, “反恐数据库判决”), Rn. 106-137; BVerfG 141, 220 (fn. 24), Rn. 305-321。
50 Vgl. Matthias Bäcker Kriminalpräventionsrecht Mohr Siebeck 2015 S. 349- 361 Dominik Brodowski Ver-deckte technische Überwachungsmaßnahmen im Polizei und Strafverfahrensrecht Mohr Siebeck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