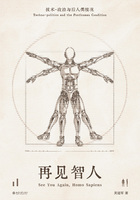
第5章 新启蒙主义抑或后人类主义
然而,晚近以来,在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主义框架,却受到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对象”(technical ob-ject)的严峻挑战。由HBO推出的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科幻美剧《西部世界》(从2016年到2022年共播出4季),显然就不是一部人类主义作品:剧中很多角色(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似乎都明目张胆地犯下了“反人类罪”。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人工智能亦一次次地刷新人们对“智能”的认知,以至于马斯克于2017年就曾联合10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发出公开信,呼吁限制人工智能的开发。他曾在推特上声称: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由人工智能开启。马斯克甚至于2019年2月宣布退出他与山姆·奥特曼于2015年12月共同创立的OpenAI,并高调宣称“我不同意OpenAI团队想做的一些事,综合各种因素我们最好还是好说好散”。[37]马斯克转而投资脑机接口项目,旨在使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能够在智能上驾驭住人工智能。[38]OpenAI推出的ChatGPT引爆全球后,包括马斯克、本吉奥以及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内的1000余位人工智能业界领袖与研究学者,于2023年3月联名呼吁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的人工智能。[39]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两个月后再次集体呼吁重视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灭绝风险,这次甚至连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本人也参与其中。
现在,人们眼里不再只有人。人类主义框架,被尖锐地撕开了一道缺口。
技术发展到21世纪,在多个具体领域(如集成电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指数级”发展趋势。在以雷·库兹韦尔为代表的技术专家眼里,当下技术的发展,很快就会把人类文明推到一个“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上,在抵达该点之后,一切人类主义叙事(价值、规则、律令……)都将失去描述性 解释性 规范性效力。人工智能,这个在其名称中就被贴上“人类”标签的“技术对象”,却正在将其创造者推向奇点性的深渊。
在物理学上,奇点指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引力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在这个奇点上,诸种科学规则和我们预言未来的能力将全部崩溃(break down)”(史蒂芬·霍金语)。[40]奇点,标识了物理学本身的溃败(尽管它涵盖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推论之中)。与之对应地,技术奇点则标识了人类文明自身的溃败(尽管它涵盖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
2017年那篇直接引发大语言模型诞生的关于“转化器”的奠基性论文的核心贡献者诺姆·沙泽尔,在一篇发表于三年后的深入研究转化器的论文结论中写道:
在一种迁移学习设置中,诸种新变体似乎为预训练中使用的去噪目标产生了更好的困惑,并且在许多下游语言理解任务中产生了更好的结果。这些架构易于实现,并且没有明显的计算缺陷。我们没有提供关于为什么这些架构看起来有效的解释;与其他一切一样,我们将它们的成功,归功于神圣仁慈(divine benevolence)。[41]
在人工智能之“智”正在快速使“智人”变成冗余的今天,当代大语言模型之“智”的核心贡献者,把这份智能归功于“神圣仁慈”——还有什么比这个“解释”,更标识出技术奇点即将来临?显然,2020年的大语言模型架构,就已使得人类主义叙事彻底丧失了描述性 解释性 规范性效力。
我们看到,在面向奇点的境况下,人类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汉娜·阿伦特在见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后,反思性地探讨“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42]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对象”正在激进地刺破人类主义框架的今天,我们则有必要反思性地探讨“后人类境况”(the posthu-man condition)。
我们也要看到,在该境况下,人类主义亦正在全力开动“人类学机器”,包括给人工智能制定“伦理”准则(比如,不能伤害人类),使它同人类“对齐”(alignment),让它懂得谁是“主人”,知晓“科技以人为本”的道理。[43]当然,那部激进溢出人类主义框架的美剧《西部世界》,很不合时宜地展示了那些遵守伦理准则、同人类对齐、通晓“科技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的前景——概言之,它们被填入到了犹太人、黑人、女人、非法移民(……)曾经占据的那些位置上。
面对人类主义铸造的这台动力强悍的“人类学机器”,存在着两种抗争方式。第一种反抗的进路,我称之为“新启蒙主义”进路:去争取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人”的范畴里来。然而,这个进路反内容不反框架。抗争者的隐在态度便是:既然人类主义话语是个典范,在这个典范内有那么多的好处,那么我得挤进来成为其中一员。它反抗的是既有的关于“人”的具体内容(如白人、男人等),其诉求是把各种被忽略、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亚人”纳入进来——通过各种各样的平权运动、女性运动、LGBT运动、Queer运动等,把各类“下等人”“边缘人”“反常人”都拉进来。
诚然,新启蒙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指向,用纳入的方式将更多被排斥在“典范”之外的“亚人”包容进来。这些斗争运动已然产生影响深远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效应。但与此同时,这一进路并没有触动人类主义的“中心 边缘”框架——“人类”被设定为最大的中心。只要这个框架不打破,总有一些群体或事物处于边缘地位——在人们眼里总有一些人看上去更像动物、禽兽,这些人就变成了“亚人”。新启蒙主义的努力,不过是多纳入一些“个体”与“群体”到人类主义框架中,把一些以前被嫌弃与抛弃的人也包括进来,让他们也成为“人”。
新启蒙主义的根本性局限就在于:总会有结构性的“余数”(remainder)。“我”进来了以后,总还会有其他的“他者”在外面,成为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余数生命”。[44]这就是所谓的“身份斗争”的尴尬。就算LGBT被纳入人类主义框架,但人们很快发现,“酷儿”(Queer)仍被排斥在外。即便Q也被纳入进来了,但总还会有当下视域里没有被看到或者看不到的个体或群体。
更致命的是,各种“亚人”哪怕在形式上被纳入,他们能否得到实质性的接纳,也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政治问题。2020年的“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抗争标识出:哪怕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性影响,60年后的美国社会中,黑人也仍然没有实质性地摆脱“亚人”的地位。“黑命亦命”刺破了现代自由主义 多元主义社会的“所有命皆命”(All Lives Matter)的陈词滥调。人类主义框架,结构性地使得一些命不算命。在吉奥乔·阿甘本看来,现代社会法律的“普遍性”,就恰恰建立在法律的“例外”之上。[45]
主张“纳入他者”的当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是新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哈氏也强调,这个“他者”必须是可以沟通与对话的、具备“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46]于是,不具备沟通理性的“疯人”,则被排斥在新启蒙主义的纳入逻辑之外——米歇尔·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哈贝马斯。[47]
能被纳入人类主义框架的“他者”,必须具有诸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属性,也就是说,那些“他者”必须足够像“人”,和典范性的“人”具有足够相似性。能够进入新启蒙主义“纳入”视域的“他者”,必须缺少彻底陌异的、激进的“他者性”。然而,在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加速时代,“他者”越来越不像“人”(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人”)——当下,比“人类”更懂策略、更有知识且更会创作的人工智能,不仅外表不像人,并且具有理性无法进入的“黑箱性”。在人类主义地平线上,越智能的“机器人”越像怪物。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犹太人恐慌”; 21世纪20年代则见证了“机器人恐慌”。[48]
第二种反抗的进路,可以被称为“后人类主义”的进路。较之新启蒙主义进路,这条进路在批判的向度上要激进得多。那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框架而非内容。该进路探讨的不是哪些人有资格进入人类主义框架中,并力图“纳入”更多的人,而是去质疑该框架本身的合理性。各种彻底溢出人类主义框架的后人类主义论述,在人类主义者眼里总是极其怪异的——譬如,后人类主义者们会频繁讨论动物、怪物、杂交物(半人半动物抑或半人半机器)……
唐娜·哈拉维在1985年就以宣言的方式,把“赛博格”(半人半机器)视作政治主体——这篇当时震撼了很多学者的言论,现在则成为后人类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一。哈拉维本来是个女性主义理论家,但在她看来,“赛博格”这个概念恰恰具有可以涵盖女性主义斗争又进一步越出其视域的激进潜能——“赛博格”打破了“自然/文化”“有机物/机器”“人/动物”“主体/对象”这些二元对立框架,“混淆”了现代性的诸种边界。[49]这就冲破了女性主义框架,亦即我们是女人所以我们为女人被纳入“人”而斗争。当哈拉维宣布“我们都是赛博格”时,人类主义框架本身亦受到了挑战。作为一种杂交的(hybrid)、复合的存在,“赛博格”无法被纳入为“人”的一种(作为“女人”“黑人”这样的“身份”),而是溢出了该框架本身。它瓦解的,是人类主义关于“人”是什么的本体论设定。
这就是后人类主义在思想史上关键价值之所在:“后人类”(并不仅仅只是“赛博格”),激进地刺出了人类主义框架。真正的批判,永远是对框架本身的挑战,而不是对内容的增减。启蒙主义者和当代新启蒙主义者尽管在把各种个体与群体纳入“人”的框架上取得了成绩,然而只要“中心 边缘”架构不被破除,就永远会有结构性的余数。从20世纪的“犹太人亦是人”(纳粹的“反人类罪”),到21世纪“黑命亦命”,人类主义者不断在原地“转圈圈”。真正有突破力量的批判性进路,是去质疑人类主义框架本身。[50]
“后人类主义”同时包含两层含义:“后 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后人类 主义”(posthuman-ism)。前者对人类主义框架构成了瓦解,后者则进一步确立起一个新的开放式框架,在其中“人类”不再占据“C位”。“后人类”指向一个开放性的范畴,换言之,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后人类”;它更像是一份邀请函,邀请各种在人类主义框架下没有位置的亚人、次人、非人(……)加入“后人类 主义”的聚合体(assemblage)中。
在后人类主义地平线上,“人”也不再是封闭式的、形而上学的“human being”,而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敞开的“human beco-ming”,不断地发生全新的“形成”——不断形成分岔、形成差异、形成新的“个体化”(乃至集体的个体化)。[51]“形成”(becoming)是吉尔·德勒兹的核心术语,旨在打破“是”(being)的形而上学闭合。当“人”处于不断形成中时,他/她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后人类”。[52]换言之,“human becoming”并不是人类主义框架下的“人”。
后人类主义拒绝把“人类”放在基础或中心的位置上,拒绝“人是万物的尺度”“科技以人为本”这样的宣称。而且,它拒绝重新定位出一个新的地基,并以此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要破除“人类”这个中心,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中心来取代,从而维系“中心 边缘”架构不变。换言之,后人类主义并不会主张以人工智能抑或动物、怪物、赛博格(……)作为新的规范性基准,并站到该“立场”上来批判人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类主义,是一种后基础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借用理查德·罗蒂的术语)的思想形态。
用人类中心主义取代白人中心主义,似乎是一个进步:它的落脚点从“白人”变成了“人类”。然而,它只是换了一个基准:从“白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变成“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思想史上的“上帝死了”事件也一样,“人”(乃至“超人”)随即被推出来占据“上帝”的位置。后人类主义取代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却在破除以“人”作为评判框架的同时,不再推出一个新的基准来占据“C位”。任何的地基,在提供给我们某种确定性的评判基准的同时,恰恰亦构成了限制我们思考的本体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