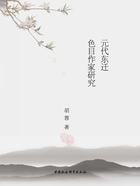
第一节 元代色目人之族源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色目人可细分为三十一种,即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若里鲁、剌乞歹、赤乞歹、畏兀儿、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剌吉答歹、拙儿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剌、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8]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中将色目人列为二十三种。[9]色目是元人对西域各民族的统称,具体所指不明确,主要部族有畏兀儿、唐兀、回回、康里、哈剌鲁、阿鲁温、也里可温、钦察等,这些部族是元代色目作家的主要来源,以下我们对此进行考述。
《汉书·西域传》描述了西域的自然地理:“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10]而本书所言的西域是广义的西域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河中地区和里海一带、直到地中海。结合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地理分布,我们把这批诗人的族源分为四部分,按照自西至东的空间顺序,首先是来自大食、波斯的回回及也里可温诗人,其次是阿尔泰山及其以北的突厥语部族包括葛逻禄、康里、乃蛮、钦察、雍古、克烈、阿速等族诗人,再次是来自天山南北的畏兀儿及其他回鹘裔诗人,最后是来自河西地区的唐兀诗人。
一 回回
在元代色目人中,东迁的回回人在全国分布很广,他们散居在从漠北至东南沿海、云南等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河北涿州的荨麻林,杭州的聚景园回回丛冢,泉州的伊斯兰教碑、云南呈贡县的回子营等遗迹就是元代民族交融的见证。元代回回人任职于中书省的共26人,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的回回人共8人,其中包括著名诗人萨都剌。元代回回诗人有:高克恭、别里沙、丁文苑、阿里木八剌、买闾、吉雅谟丁、哲马鲁丁、沙班、马世德、丁鹤年、吴惟善、爱理沙、萨都剌、伯笃曾丁、大食惟寅等。“回回者,西北种落之名,其别曰答失蛮,曰迭里威失,曰木速鲁蛮,曰木忽,史称大食、于阗、拂林者,皆回回也。”[11]在元代,回回一词兼有民族名称和伊斯兰教徒两重含义,“‘回回’是元代对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人的称呼。它泛指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突厥人等在内。伊斯兰教徒早在元朝以前就已经来到中国(如唐、宋时期到达广州、扬州、泉州等地的大食人和波斯人),仅到元朝才大批前来并定居中国,并被称为回回,成为我国回族的先民”[12]。唐朝就有“回回”一词,指回纥(回鹘)等突厥族人。伊斯兰教是10世纪传到西域的,元代才有回回人的说法,穆斯林的寺院称“回回寺”,元代是回回人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回回人涵盖了多个民族,如葛逻禄和阿儿浑两个部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是回回人的一部分,但以族名相称。钦察人、康里人、阿速人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还不明确。回回人与畏兀儿人的宗教信仰不同,畏兀儿人以佛教为主,他们称为“偶像教”,“畏吾儿人采用偶像教为他们的宗教,其他部落大多仿效他们的榜样。谁都比不过东方偶像教徒之执迷不悟,谁都比不过他们之敌视伊斯兰”[13]。于阗等地的畏兀儿人信奉伊斯兰教,已称作回回人。陈垣和杨志玖都对萨都剌的族属进行了详尽考辨,一致认为,萨都剌是回回人[14]。元代还有一个氏族名称答失蛮,《西湖竹枝集》称萨都剌为答失蛮。这个名词来自波斯文,指伊斯兰教士,含义是学者、明哲的人。答失蛮还是人名,《元史》中出现12个答失蛮的人名。[15]
元代的也里可温诗人有:雅琥、金哈剌(金元素)。“也里可温”在元代又称作“迭屑”“迷失诃”“聂斯脱里”。“也里可温”一词指元代中国的基督教徒,与僧、道、答失蛮等宗教信徒并称;也指元代一个西域民族,与乃蛮、回回等其他色目民族并称。“也里可温”与“回回”一样,兼有宗教和族群双重内涵。元代基督教寺院称“也里可温寺”“也里可温十字寺”“十字寺”。元亡后,也里可温就消失了。[16]
余阙在《合肥修城记》中称马世德是“也里可温人”。戴良《鹤年吟稿序》将也里可温与回回等其他西域族群并称:“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17]
二 北部突厥语族
畏兀儿、唐兀、回回是色目作家群中人数占比较高的民族,康里、哈剌鲁、乃蛮、钦察、雍古、克烈、阿速、阿鲁温等天山以北突厥语各民族也涌现出杰出的诗人。
元代康里作家有:不忽木、巙巙、回回、拜住、察罕不花、康里百花等。康里源自古代高车人,又称康礼、航里、抗里、夯力、杭斤等,6世纪中期,突厥兴起后,康里人隶属于突厥,和哈剌鲁一样,属突厥人的一支。突厥灭亡后,被葛逻禄人所统治,8—11世纪,康里人游牧区域是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地区。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和《金史》记载,12世纪时,西辽和金朝崛起时,一些部族曾臣服于西辽和金朝。13世纪初,花剌子模国成为中亚强国。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母亲秃儿罕可敦是康里伯岳吾部族人,在其专权时期,康里人在军中深受新任,大量康里人南下,在花剌子模军队服役,当时驻防撒马耳干的11万军队中,有6万是康里人。这一时期,康里人的领地广阔,包括乌拉尔河以东、咸海以北,伊塞克湖和楚河一带,还活跃在波斯、呼罗珊及河中地区。
哈剌鲁,即葛逻禄,在元朝又称合儿鲁、匣利鲁、罕禄鲁、匣禄鲁、柯耳曾等,是突厥的一支。“Qarluq:汉文作葛逻禄,为著名突厥部落之一。原居于北庭(遗址在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一带)之西北,阿尔泰山之西。8世纪中期曾与回鹘、拔悉密(Bashmil)一起灭掉突厥汗国。后迁移到七河一带。8世纪后半期已到达毗邻喀什的费尔干盆地。有的学者(如O.Pritsak)认为建立喀拉汗朝的为葛逻禄突厥人。”[18]《元史氏族表》记载:“哈剌鲁氏亦称罕禄鲁氏,本西域部落。太祖西征,其国主阿儿厮兰率众来降,封为郡王,俾统其部众。其裔孙帖木迭儿,顺帝之外王父也。”“合鲁氏亦称葛逻禄氏,本西域国。世居金山之阳,其后散处内地。”“乃贤亦合鲁氏,自南阳徙居浙东。”[19]《新唐书》中记载有葛逻禄的历史:“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与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20]葛逻禄曾附属于回鹘,属于回鹘十一部落之一,唐肃宗时期开始强大起来,789年脱离回鹘独立。[21]漠北回鹘被黠戛斯打败后,西迁回鹘的其中一支“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22],葛逻禄与回鹘会合于楚河一带,并联合于10世纪建立喀喇汗王朝。葛逻禄在12世纪时居住在中亚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13世纪初归附于成吉思汗,部分族人陆续东迁,在中原内各地定居。元人危素为廼贤诗稿作序时曾言及葛逻禄的历史和东迁葛逻禄人的情况:“易之,葛逻禄氏也,彼其国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国远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与回纥最先来附,至今已百余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然则葛逻禄氏之能诗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见我朝文化之洽,无远弗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23]
元代阿儿浑诗人有:掌机沙、答失蛮彦修、仉机沙等。阿儿浑人,也称为阿鲁浑、阿鲁温、阿别温、合鲁温、阿鲁虎、阿剌温、阿儿温、阿剌浑等。具体方位是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即吉尔吉斯共和国全部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一部分。[24]这一地带是10世纪下半叶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领地,因此,阿儿浑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的哈只哈心家族,杨维桢《西湖竹枝集》提到的掌机沙及哈散家族,都是阿儿浑的伊斯兰信徒。贡师泰《玩斋集》卷八《双孝传》中,也记录了一个阿儿浑的伊斯兰家庭,亦福的哈儿丁,祖父叫扎马剌丁,儿子叫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沙。阿儿浑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南京、镇江、安庆、漳州、嘉兴、杭州等地都有阿儿浑人。
阿速人,西方文献称为阿兰人,号称“绿睛回回”,是从高加索地区迁来的西域人。据王桐龄考证,“阿速,《汉书·西域传》称奄蔡,《后汉书·西域传》称阿兰聊(西罗马末年之Alan),其邻国后汉时有粟弋(西罗马史之Suevi),《魏书·西域传》称粟特,一称温那沙(西罗马之Uandals),与东、西峨时同族,实阿利安中条顿民族也”[25]。
诗人泰不花是伯牙吾氏,“伯牙吾氏又有泰不花”[26],伯牙吾氏即钦察人,“钦察者,西北部落,其先曲出,自武平折连川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所居伯牙吾山,为氏,号其国曰钦察。”[27]“公(土土哈)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辙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产宜马,富者有马至万计。俗衽金革,勇猛刚烈,盖风土使然。”[28]
三 畏兀儿
有元一代,东迁色目族群不仅人数多、地域分布广,而且政治地位高。其中,大批畏兀儿人入居汉地和蒙古高原,出任元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元史氏族表》就列出畏兀儿族31个家族入仕元朝,这些家族人才辈出,活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29]其中不少在文学方面都颇有成就,如孟速思、小云石脱忽怜、贯云石、安藏、伯颜不花、廉希贤、廉希贡、廉惇、马祖常、偰玉立、边鲁等。[30]在色目作家群体当中,大都闾、三宝柱、脱脱木儿、纳璘不花、伯颜不花、倚男海涯、廉普逵、马昂夫、的斤苍涯、谢文质海牙、王嘉闾、马祖常、廼贤、贯云石、康惇、边鲁、偰玉立、偰哲笃、偰逊、赵世延、盛熙明等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为畏兀儿文学史增添了华彩的乐章。
元人通行的诏令文书中,畏兀儿还被称为辉和尔、辉和、畏吾、畏兀、畏吾尔、乌鹆、委吾、瑰古、委兀、伟兀、畏午、畏午儿、卫兀、卫吾、外五、外吾、畏吾而、伟吾而、卫郭尔等。元人认为畏兀儿就是唐代的回鹘。欧阳玄在《高昌偰氏家传》中说:“回纥即今伟兀也”[31];而王恽则在《玉堂嘉话》中说:“回鹘今外吾。”[32]《元史氏族表》辨析了畏兀儿的名称,认为高昌北庭就是畏兀儿族,提及在元代很多畏兀儿人入元朝为官,高昌国王与元庭世代通婚友好等情况,“畏吾儿者,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或云伟兀,或云卫兀,或云卫吾,其实一也。回鹘牙帐本在和林之地,唐末衰乱,徙居火洲,统别失八里之地,唐北庭都护所治古高昌国也。太祖初兴,其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举国入觐,太祖以公主妻之,自是世为婚姻。国人入仕中朝者,多知名者。亦都护,华言国王也。凡史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33]
畏兀儿的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游牧在我国西北至贝加尔湖一代的“丁零”,5、6世纪游牧在鄂尔浑河和天山一带,史称“铁勒”,7世纪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回纥汗国。元人文集多处提到畏兀儿祖先最初居地是在今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之间。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记载:“退而考诸高昌王世家,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树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十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传三十余君,是为玉伦的斤,数与唐人相攻战。久之,乃议和亲,以息民而罢兵,于是唐以金莲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励的斤,居和林别力跛力答,言妇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言天灵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34]“公讳亦辇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国中有两树,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婴儿,四儿死,而第五儿独存,以为神异,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让以国,约为世婚,而秉其国政。其国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35]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也记载畏兀儿人的原居住地在漠北斡儿寒河一带,“畏兀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河畔,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剌和林的山中;合罕近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有三十条河发源于哈剌和林山;每条河的岸边居住着一个不同的部族;畏吾儿人则在斡儿寒河岸形成两支。当他们人数增多时,他们仿效别的部落,从众人当中推选一人为首领,向他表示臣服”[36]。
在漠北高原这个大舞台上首先出现的突厥汗国,之后是回鹘汗国。《周书》记载,突厥本是匈奴的一支,生活在阿尔泰地区,突厥一词首见于史册是公元540年,550年突厥破铁勒,552年突厥建立汗国,灭柔然,整合铁勒诸部,统一了整个漠北地区,统辖大兴安岭到咸海的大片区域。铁勒之中的袁纥、仆古、拔野古、同罗等部落联合起来反抗突厥,这个联合体称为回纥。[37]唐初,唐朝与回纥联合消灭了突厥,铁勒诸部统称回纥,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回纥(鹘)汗国雄踞漠北近百年(745—840)之久,《旧唐书》卷195之“回纥传”,《新唐书》卷217之“回鹘传”,《唐会要》卷98之“回纥”,《宋史》卷490之“回鹘传”等历史文献都记载了回鹘发展的历史。
《旧唐书》中记载:“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象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革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其,以寇抄为生。自突厥原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38]
唐朝与回鹘关系密切,回鹘和其他游牧部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安史之乱时期,回鹘派叶护可汗率兵4000人协助平叛,收复长安、洛阳。840年,回鹘外有黠戛斯的攻击,内部发生内乱,加之大雪、瘟疫天灾不断,回鹘被迫离开漠北故地,一部分人南下,大部分西迁。一支迁徙到河西地区,以张掖为中心,分布在甘、凉、瓜、沙等州,称“甘州回鹘”“河西回鹘”,11世纪,党项族占领河西地区,河西回鹘从此隶属西夏。另一支迁至葱岭以西,参与建立了辖地广大的喀喇汗王朝。1129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消灭喀喇汗朝,建立了西辽政权。还有一支迁到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集中在西州一带,以高昌(元代称火洲)为中心,这支回鹘称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元人认为高昌回鹘是漠北回鹘的嫡传,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载:“玉伦的斤薨,自是国多灾异,民弗安居,传位者数亡,乃迁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火州也。”[39]《元史》记载:“乃迁于交州,交州即火洲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居是者凡百七十余载,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40]
高昌回鹘不断壮大,高昌成为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当地其他部族也逐渐融入回鹘,回鹘逐渐成为新疆的主要民族,其辖境广阔,东到河西,西达葱岭,南临大漠,北越天山。北宋初期,龟兹地区已生活有回鹘部众,《宋史》载:“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币,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行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41]
从漠北高原到吐鲁番盆地,回鹘人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迁后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宜于农耕,他们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开始定居,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经济。蒙古高原发现的回鹘汗国时期的碑铭见证了漠北回鹘的历史,主要有碑铭有《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也称《葛勒可汗碑》或《磨延啜碑》)、《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又称《哈拉巴喇哈逊碑》)、《苏吉牌》、《塞富莱碑》、《塔里亚特碑》(又称《铁尔痕碑》或《磨延啜第二碑》)、《铁兹碑》(又称《牟羽可汗碑》)[42]等,这些碑铭记录了畏兀儿民族发展的历史。1957年在杭爱山铁尔痕河谷地铁尔痕查干淖尔湖附近发现《铁尔痕碑》,记录了早期回鹘汗国751年前后的事迹:“所有四方的人民都(为我)出力,我的敌人则失去自己的福分……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ya和buryu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43]
著名蒙古史学家屠寄说:“唐代回鹘举国师佛,及为黠戛斯所破逐,其一支西奔葛逻禄,转入大食波斯故地,种人改信天方教。前史仍称为回鹘或回回。一支奔据高昌兼有北庭都护府故地者,语讹为畏兀仍以佛法为国教,故有元一代,畏兀文人入中国者,如安藏、阿鲁浑萨理、洁实弥尔等皆通知内典,传译经论。而唐仁祖、燕只不花、脱烈海牙、普颜等,濡染华风,则又各有当官之效焉。安藏虽习浮屠兼好儒术,屡与许衡以儒者之言进劝时主。尤难能也。阿鲁浑萨理依阿权相,交通东宫,外君子而内小人,虽博学多才,适足文其奸?”[44]因此,陈高华先生说:“兼通佛学和多种语言文字,是这一时期不少畏兀儿人共有的文化特色。”[45]
四 唐兀
除了畏兀儿外,唐兀诗人在元代色目作家中也占很大比例。元代唐兀作家有:张翔(雄飞)、余阙、买住、斡玉伦徒、孟昉、王翰、甘立、琥璐珣、昂吉、完泽、贺庸、李琦、观音奴(鲁山)、观音奴(志能)、拜帖穆尔、高纳麟、必申达儿、杨九思、塔不歹、刘伯温(沙剌班)等。
“唐兀”指西夏党项羌人,元太祖灭西夏后称西夏部众为唐兀氏。唐兀一词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辽代就称党项羌为唐古,蒙古人称之为唐古忒或唐兀惕。陕、甘、宁一带的黄河以西地区是西夏的辖区,元代文献中称为“河西”,元人吴海云:“河西,古诸羌。宋李元昊据以为边……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因此,唐兀即指西夏人或党项羌人、河西人。
《元史氏族表》记述了西夏国的发展史:“唐兀者故西夏国,自赵元昊据河西与宋、金相持者二百余年,元太祖始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仕宦次蒙古一等,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然仕宦者皆舍旧氏而称唐兀氏云。元昊本出拓跋部落,唐末始赐姓李,宋初又赐姓赵,国亡,仍称李,居贺兰于弥部,又号于弥氏,或称乌密氏,亦称吾密氏。太祖经略河西,有守兀纳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子惟忠。”[46]
公元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西夏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大体上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及陕西、内蒙古一部分。主要民族有党项、汉、吐蕃、回鹘、鞑靼等,党项为西夏的主体民族。西夏立国近二百年之久,先后与北宋和辽、南宋和金政权并存。[47]
元代,西夏故地仍称“西夏”“中兴府”旧名,先后设立的管理机构有: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西夏宣抚司、宣慰司、宁夏路行中书省等,1286年,设甘肃行省,辖区基本是西夏故地。西夏故地泛称河西,唐兀人仍居住在这里。河北邢台人张文谦在行省西夏中兴等路时,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邢州学派的郭守敬疏浚了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并开辟新渠,唐兀人得以安居乐业。[48]
元代唐兀人英才辈出,如元统元年共录取色目进士二十五名,其中就有八名唐兀人。他们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元朝时在中央和地方做官的唐兀人达六十余人。[49]
从文化传统方面看,唐兀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畏兀儿、吐蕃、回回、也里可温等族有较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拥有本民族知识分子,而康里、哈剌鲁、钦察、阿速等游牧部落的文化水平不高,与中原文化亦无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