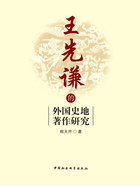
第一节 晚年疾病缠身的王先谦坚持完成外国史地著作的缘由
孙玉敏《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将王先谦的生平分为几个时期,其中京华二十年(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一年,即1865—1885年,近二十年的时间)是王先谦学术积累期,也是厚积薄发时期。辞官后的三十年里,王先谦写了大量著作。[1]在王先谦不到77年的人生历程中,其后半生的46年(1872—1918),几乎每年都有著作,甚至去世前一年还在著述,甚至一年数部。王先谦的三部外国史地著作,是在王先谦晚年完成的。
1889年王先谦脱离官场回家专门著述,叶德辉在《葵园四种》跋中谈到王先谦自回里后,“二十余年,无日不从事文字之役”[2]。王先谦这种生活的心态,可以从其1910年所写小诗《休官》看出,“我生勇决不如人,只有休官浑舍嗔。赢得读书清静业,乞还随俗笑谈身”[3]。其一“赢”与一“笑”,活现了王先谦晚年潜心著述时内心的无限快乐之情。
虽然内心是快乐的,但是晚年王先谦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他时时要和病痛做坚强的斗争,才能把著述工作进行下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刻《汉书补注》百卷成,“虽病剧,书不释手,中情怫郁,舍此亦无消遣。……了此大愿,亦一喜也。”[4]时年59岁的王先谦,不顾病痛,仍以著述为“消遣”。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先谦61岁,完成了《日本源流考》。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先谦64岁之时,开始编辑《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图志略》,他深感“造端宏大,年力已颓,未卜果能竣事否也。”[5]担忧之情虽溢于言表,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先谦66岁时,健康状况更遭,“余头眩之疾,已愈数年,四月中复发,倾跌一次,幸未中风痰。天祖大恩,感谢何极!从此闭关谢客,不敢出厅户一步矣。”同年(1907),督抚推荐他做湖南学务公所议长,王先谦觉得自己“衰年多疾,于公务更复何裨?”[6]宣统三年(1911),70岁的王先谦,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余右手二指麻木,不能作书,闻江苏有针医尤姓,于六月二十日买舟前往就医,竟无存效。而右颧发际忽生一疮,洪大肿痛,证极危险,延刘姓医治,越日即溃,遂邀刘同归,又匝月始愈”[7]。
王先谦身体状况如此之差,不得不把更多时间、精力耗费在看病上,给他所钟爱的著述工作无疑造成了极大障碍。
即使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之下,王先谦仍于其生命最后十余年(1908—1918)完成了《葵园自定年谱》《五洲地理志略附图》《后汉书集解》《元史拾补》《外国通鉴》等多部有分量的著作,其毅力之坚韧,不能不让后学者由衷佩服。1901年王先谦重刊《景教纪事碑文考证》一卷成,1907年阮元阅读后赋诗一首,盛赞王先谦的治学精神,“葵园著书有真乐,才力纵横气磅礴。苞孕九流屯七略,函富琳琅庋盈阁。就中新刊景教编,乃出番禺杨氏作。公为制序论源流,使我读之意寥廓”[8]。
正在王先谦著述《日本源流考》之时,1899年他通过与日本宗方北平[9]的通信,表达了心声“生平耽嗜文艺,一息未死,犹思有所述作,以诏往来”[10],恰为他晚年写作完成外国史地著作的心情。
经多年学术积累,王先谦形成了对文章反复修改、校订的严谨治学风格。光绪九年(1883),完成校刊《新、旧唐书合注》,序曰“予于二书,反复积年,颇有考订”[11]。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作《汉书补注》序,“时有改订,忽忽六旬。炳烛馀明,恐不能更有精进。忘其固陋,举付梓人”[12]。王先谦写作外国史地著作,也把这种习惯延续了下来。
宣统三年(1911),王先谦在《此生》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学术的强烈热爱之情,“此生何幸老书林,斗室纤尘了不侵!开卷如逢今日事,定文时见昔贤心”[13]。
王先谦晚年撰述外国史地著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由:
其一,王先谦认为中国对于域外的研究应有专书讨论,解释清楚模糊问题。在书信《与但方伯》中,王先谦提出研究域外之重要性。“即讲求中国舆地,考古通今,尚非难事,若域外之观,止能得其大概。至疆域之细目,古今分合之源流,宜别有专书,因当俟之异日者也。”[14]
1906年,清朝总理学务大臣审订《瀛寰全志》,透露了对以前地志的叙述缺陷的忧虑,“地志一书,坊间罕有佳本。非本国过略,即外国不详”[15]。即很多地理志对中国的叙述过于简略,或对外国的叙述不够详细。王先谦所著的《五洲地理志略》照顾到了不同国家,尽量囊括更多的国家。
其二,提倡学习日本,不支持盲目学习。
1902年《日本源流考》刊行,王先谦主张学习日本的长处,但不支持对日本的盲目学习。孙玉敏认为王先谦由于年老多病推脱了湖南图书馆总理的职务,编撰《五洲地理志略》是受湖南巡抚端方的委托。[16]这是直接原因。本书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王先谦认为不能盲目学习日本,他编撰《外国通鉴》与《五洲地理志略》是对这种状况的回应。光绪三十一年(1905),“仿日本例开设图书馆于会垣”请王先谦总理馆事,“余谢不敏,允为编纂新学数部,以塞其意。于是有编辑《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之举”[17]。
总之,王先谦晚年编撰外国史地著作,既有从学术角度考虑的因素,也有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因素。一方面要写出一部集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了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的人生夙愿。这是他即使在身体状况非常差的情况下,也要完成外国史地著作的根本缘由,这也是王先谦由早年研究中国传统典籍到晚年撰写外国史地著作的学术转型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