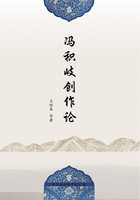
第4章 《永远的苦难之旅》:饥饿
冯积岐的小说具有苦难、忧郁的气质,似乎这些人类永恒情感的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长在了他的身体里,与生俱来,如影随形,挥之不散。这种苦难、忧郁的感情种子一旦碰到适合生长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快速成长。不知幸运与否的是这种子真的碰到了合适的土壤,在作者身上、在他的小说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说其幸运是因为正是这种子成为作者的气质,成就了其小说的独特品质;说其不幸是因为这种子碰到的土壤的养分却是酸涩、苦难的,作者的气质、其小说的特质都是在这种养分中成长和获得的。
苦难在冯积岐的笔下呈现为多种形式。从苦难承受者角度来看,苦难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当然就冯积岐的小说写作历程来看,苦难最初表现在个体或者几个人身上,最后表现在群体身上,这表现出了作者把握生活的能力和观察主体的能力,也是作者主体创作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的显现。从苦难的内容来看,冯积岐小说中的苦难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者以饥饿、疾病、金钱匮乏等物质形式表现,或者以性欲不满、权力戕害等精神形式表现。这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生活体验的敏感性。从苦难所表现的内质来看,在冯积岐小说中,大多表现出的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即人类苦难和困顿性的一面,生活中欢乐和幸福的一面似乎遥不可及,总被这些苦难遮蔽着。总之,冯积岐的小说总是在诉说着人类的苦难,而且这种苦难呈现出不能完结性——成为永远的苦难之旅。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主人公一直都是敏感、忧郁的,似乎在他身上人性中欢乐和幸福的一面都被生活的苦难所遮蔽,生活呈现给他的永远是忧伤和艰难,这成为其小说主人公生活的主基调和主色彩。他或者被时代所压迫,或者被同时代的人所压抑,在这种大小环境的双重压制下,主人公注定不能摆脱其苦难的生活与苦难的人生。另外,这种苦难的特质不仅表现在主人公身上,也表现在主人公所代表的特定群体身上。当然这种苦难并非是一开始就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的内容是双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有,但最终都以精神的痛苦为主,这其中渗透进作者多重的观察视角,也有其在这一方面写作的路数,那就是物质上的痛苦最终将转变为精神性的痛苦,苦难总以精神痛苦的形式向读者展示,相比较而言,物质上的困顿和苦难似乎成了精神苦难的对比物,物质上的苦难最终似乎变得微不足道,而精神的困顿和苦难似乎总也逾越不了,它像个幽灵一样总徘徊在冯积岐的小说中。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是人类生活的内质,似乎人类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这种苦难以其不可完结性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表现出来,不仅表现在其众多的短篇小说中,还在他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中。
冯积岐的小说与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分不开,在他的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就在苦难中汲取生存的养分;他讲述了自己在1979年被纠正成分后,积极投入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开始写作。他的青年时期是在写作中证明自己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证明’建立在他人的肯定和承认之上是很痛苦的事情”[1]。他对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认为,他说:“我不可能像我的祖母一样,把自己在文学上的创造和价值建立在当代的某些人的认同或褒奖上。我顽固地相信,只有时间才是最好的证明。”[2]在他看来,真正的证明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能干什么、干不成什么”[3],而是对“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所理想的高峰”[4]的迈进。所以他在青年时期的写作正如他一再强调的:写得很苦。这种苦,除了身体上的,从家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医院的身体之苦外,还有自身对于写作的绝望、对于人性复杂性和宽广性的不断探寻所产生的精神痛苦。这些在冯积岐的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苦难表现在人最应该幸福、最应该欢乐、最应该对未来生活抱有美好想象的少年时期;表现在人最应该奋斗、最应该积极、最应该对未来激情澎湃、最具有冲击力的青年时期。苦难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是有原因的,这与冯积岐的自身经历有关。冯积岐在其访谈录里讲道:“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脸上被刻上了‘红字’。最使我痛苦的是,我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一个‘狗崽子’的艰难人生我就不细说了。我开始了不是人的人生。我的生活状态如同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中的老鼠,即使在地洞中也是惴惴不安。在以后的青年和中年的前半期,我左冲右突,总是冲不出心理上的囹圄。”[5]他还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村和我年龄相仿的地主‘狗崽子’有三个自杀了。我也曾自杀过——用两颗钉子系住一根绳子去上吊,结果,钉子抽脱了,自己跌在了地上。”[6]这可以看出,他的少年时期过得极其压抑,这些话给了我们分析冯积岐小说的入口,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应幸福、欢乐、对未来抱有美好幻想的少年成了一个惴惴不安、毫无安全感的病态孩子。这种状态并不只是来自于物质上的压力,更多是来源于精神,在冯积岐的访谈中,他甚少谈到物质生活的困顿和匮乏,谈得最多的反而是对于知识探求的不可得所带来的痛苦,最使他痛苦的是他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冯积岐所认为的苦难是一种心灵上的,也就是他后来所讲的“我确实历经了其他和我同龄的作家很少历经的苦难,这不仅是饿过肚子,要过饭。创伤主要来自人格的凌辱,自尊心的伤害,尊严的被践踏。心灵的苦难才是苦难的真正块垒”[7]。这直接导致了他认为的“不是人的人生”,而这种不是人的人生使他的心理状态即使在安全的物质环境下,仍然惴惴不安。这种苦难比物质上的苦难更能折磨人,也更能消弭人的精神。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描写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性格不同,面貌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生活悲惨,大多都经历过苦难的生活,身体和精神在苦难的生活中都受到磨炼。在他的小说中,身体的苦难大多来自于饥饿、病痛、性压抑;精神性的苦难大多来自于权力;小说中所呈现出的苦难以身体苦难为基础,继而上升为精神苦难。总之,这些苦难以饥饿、性、病、死亡等形式表现。
——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饥饿图景,但大多都是对于饥饿感的描写,这种描写大多都是主人公少年时期的感受。他在《敲门》中描写了十三四岁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饥饿景象,“母亲给丁小春说……母亲实在走不动了,就撅坡地里的野草吃。不要说那野草是什么味儿,只要能撅得动只要能咽得下,母女俩就吃,哪怕那野草含有毒汁毒素,哪怕那野草吃下去当即毙命,只要当时能把肠胃填一填。母女俩大嚼大咽,以致嘴角里绿水长淌,口腔里发涩发苦发麻,直到失去味觉。母女俩像牛一样贪婪地吃着野草,边吃边走”。而丁小春的母亲在叙述饥饿感时说:“人一旦饿极了,不要说吃草,看见石头都想吃。饥饿不但折磨人的肉体,也折磨人的心性。母亲说,外婆为了要一把面,把比自己小一辈的小媳妇叫姨叫婆。母亲说,假如有人把刀给她架在脖子上,她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但在饥饿面前,她不屈服是不可能的。”[8]而这并非作者众多小说中的独一场景,在他的《关中》中,他描写了三年困难时期一群沦落为叫花子的“甘肃客”的饥饿景象。“甘肃客”都聚集在村子东边的地窖里,为了活命,大多女性和孩子就跟村里的光棍汉们生活在了一起,不问年龄,不问美丑,只要能活命。而忍受饥饿的孩子被人收留后,当“我问朋友,想不想他的亲生父母?朋友说,不想。我说,为啥?朋友说,亲生父母没有养活我长大成人。对朋友的这种感情,我很难过……饥饿改变个人的感情和性格”。饥饿让19岁的少女与村里40多岁的中年人生活在一起,而村里偷苜蓿的三个年轻女人,顾不得廉耻也要留住偷来的苜蓿,甚至有一个女性把裤子脱下来装苜蓿,当村里人要抢苜蓿时,她更是死命抱着不放。《沉默的季节》中宁巧仙为了200斤粮食,被六指占有,周雨言也讲:“饥饿是一种饱胀的感觉,是对食物强烈的难以抑制的欲念撑破肚皮的饱胀,欲念使你惶惶不安使你无可奈何使你丢弃了所有的标准规则而不顾,只想去满足你的欲念,即使你当即死去,欲念也不会随着死亡而咽气,它还在跳跃,在撺掇你去制服它或克服它。饥饿像一个打手,将我的意识越挠越清晰。”[9]周雨言的母亲因为饥饿难耐,“将手伸进了主人家的猪食槽里去抓吃一块被主人丢弃的高粱面搅团,主人发觉之后,以为她是一个明目张胆偷人的贼,就将她的头颅硬向猪食槽里按”[10]。在冯积岐的笔下,饥饿不仅给人的身体带来不可抗拒的伤害,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摧残,人变得没有尊严,没有羞耻感,以至于人的亲情也会因为饥饿而消失殆尽。正如作者所言:“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饥饿确实会扭曲人性,使人变得像狼一样凶。饥饿太神圣了,饥饿太残酷了。”[11]饥饿的感觉不仅来自于肠胃,来自于身体,它还会上升为精神内容,改变情感,扭曲性格,让人顾不得尊严,使人性扭曲,这成为冯积岐小说中探寻人性复杂性的一个入口。
注释
[1]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2]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3]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4]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5]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6]李继凯:《复杂人性的探寻和文学生命的建构——关于冯积岐小说创作的对话》,载李继凯主编、苏敏选编《冯积岐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页。
[7]吴妍妍:《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
[8]冯积岐:《敲门》,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9]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10]冯积岐:《沉默的年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11]冯积岐:《关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