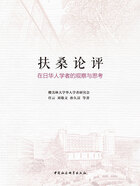
四 “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评价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僵化,特别是金融系统结构固化以及企业系统出现了制度疲劳症,以及政治与政府在改革传统制度上的滞后或不作为等复合因素,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以及TFP增长率的停滞,这应该是日本经济出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后小泉时代的历届政府多数都意识到了放松管制及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性,民主党执政三年期间,菅直人还提出了“第三次开放国门”的改革口号,但由于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反对势力的抵抗,改革步伐缓慢甚至倒退。2012年底随着安倍再次掌权,其所提出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经济政策的亮相,标志着改革的重新启动。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从2012年11月第二次竞选日本首相开始,着力推动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总称,旨在帮助日本经济摆脱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的长期困扰,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安倍经济学主要由他自诩的“三支箭”所组成:第一支箭是大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是机动的财政扩张政策;第三支箭则是旨在刺激民间部门、提高经济活力的经济增长战略。上台伊始,安倍便射出了头两支箭,而最后一箭直到2013年6月才射出。
安倍上台两年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一定的复苏迹象。但量化宽松金融政策难以实现两年内物价上涨2%的预定目标,对金融政策的效果评价也为时尚早。而财政政策一开始便遭到了较多质疑和批评。关于安倍经济学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日本国内外已有诸多评价,[45]相比较而言,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瞄准了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本质问题——僵化的经济体制和过度的管制制度。本节我们重点分析第三支箭即增长战略。
该增长战略在2013年6月出台时主要项目可归纳为:(1)促进产业新陈代谢。通过实施新税制,促进民间企业增加设备投资;激活IT网络融资和风险投资,支援创业,提高开业率水平,推动企业加速重组和兼并等。(2)提高人才水平。通过提升劳动力流动性,以及提高劳动人口中年轻人及老年人特别是女性的就业率,改进大学教育,吸引海外高级人才赴日工作等方式,改善日本的劳动力要素。(3)增加区域竞争优势。设立东京、大阪、爱知等国家战略特区,放松管制,大幅度改善外国人的各种环境和生活条件,创造世界最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4)大幅度放松管制,提升日本IT、医疗健康、能源、农林水产、旅游观光以及贸易等产业的竞争力和活力,开拓新产业前沿。(5)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日欧FTA,在三年内将FTA贸易量占总量之比从20%提升到70%左右,并努力拓展海外大型公共工程等业务;等等。2014年6月,经过一年的实践,安倍又将增长战略提炼为四句话,即(1)通过放松管制改革以及减税等措施,以促进投资增长,激发民间活力;(2)创造良好环境,以更好地发挥女性、青年及老年人的潜力,激活人才市场;(3)创造新产业及新市场,以应对人口出生率降低及高龄化,力争成为解决高龄化问题的先进国家;(4)加快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世界的企业走进来。
上述基本方向应该说瞄准了日本产业新陈代谢能力不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等关键问题,也体现了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的意向。
截至2015年3月底,我们发现增长战略在一些领域还是有所突破的。如从2013年12月通过的《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国家战略特区关联法案》以及涉及农业和医药改革的相关法案来看,安倍政权对原有制度或结构有所冲击。特别是决定在今后五年之内废除农地休耕政策(减反政策),成立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比重,以及放宽对大部分医药品网购的管制等政策,表明现政权正在一些领域冲击多年来强固利益团体所构筑的坚如磐石的防线。2015年1月,政府及自民党所提出的对金融、证券分析等5行业年收入超过1075万日元的白领阶层普通员工(不含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实施与劳动时间脱钩的弹性作息及绩效工资制度的改革法案基本定型。而2015年2月初,自民党政权经过多回合的较量,终于与全国农业协会中央就农协组织这个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改革方案也达成一致意见:将农协中央全会改建为一般社团,剥离其监察职责,撤销其对地方农协的监察及指导权限,以鼓励地方农协独立自主经营;同时将以往承担农产品营销业务的全国农协合作联社改建成股份制企业,以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说农协组织成立60年来终于迎来了大变革。此外,增长战略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法人税减税,2014年3月提前一年取消了临时设立的震灾复兴税,下降2.4%,从2015年4月起法人税率将进一步下降2.51%,法人所得税率降至32.11%。
不过,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改革则显得力度不足,或是与当初设想相比退步。如鼓励创业项目提出三年内将企业创业开业率从2013年6月的4.5%提升到10%以上,直到2014年3月20日,中小企业厅才公布了第一批支援的地方自治体名单94家(仅占全国地方自治体总数的5%),而且主要支援政策是设立创业指导窗口、开办辅导班,对创业者的经济扶持仅限于降低工商登记税费、扩大担保信用额度,其政策扶植力度还不如中国的大学生创业支援;还有,政府提出增加女性就业率,将女性管理职位比例从近期的11%提升到2020年的30%,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就是号召上市企业主动公布女性干部人数等数据,据内阁府报道,截至2014年3月也只有32%的企业公布。从这些例子可管中窥豹:安倍增长战略的各项目的实际推进力度还不平衡,这一点也是日本国内外学者的共识。[46]
笔者认为除推进力度不够平衡之外,安倍增长战略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如何触动民间经济制度及结构改革这一重要领域。如前所述,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与金融系统和企业制度处于严重的僵化及制度疲劳状态有密切关系,为此政府需要在相关法律及制度改革方面拿出更多的意见或政策来推动金融体系与企业制度变革,但安倍增长战略中难以看到这样的内容。[47]以企业制度改革为例,尽管在《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里提出了一些促进产业重组及再建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增长战略基本没有涉及公司法修订,比如现有法律中有关公司重组及法律清算的条款均有制约企业新陈代谢的问题,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披露内容也有待于扩充,这些重要制度的修订没有提上日程,连增加外部独立董事以加强企业治理的意见虽经过多年讨论也难以写进法规。[48]在雇佣制度改革方面,尽管政府最近终于就年收入超过1075万元的高薪阶层实行弹性工作及业绩工资制达成一致意见,但针对人员和行业极其有限,迄今为止政府没有任何其他提高正式员工雇佣弹性的实质性改革措施,雇佣法关于解雇的规定等也难以撼动。在金融领域,政府在2014年3月提出了《促进民间非正规金融融资修正法》交由下期国会审议,旨在放开创业企业通过互联网集资的管制。关于培育风险投资基金,政府只是在《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里提出了对大企业建立创业基金的税收优惠制度,而在整个金融结构及制度的设计方面没有着力。诚然,金融系统结构和企业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且有些制度是不成文的习惯和传统,其问题并非都能通过政府主导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但政府通过修改法律给予企业在法律上新的约束,或放松管制给民间企业提供制度改革的空间,将诱导或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改革其经营模式,加速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真正长期有效的增长战略,应该更多思考如何更好地带动民间经济主体行动起来,加快民间主体主动革除其自身体制弊端,创新经营管理模式的进程,而不仅仅靠财税优惠的诱导,使得企业因有依靠而滋生惰性,降低革新僵化制度的紧迫感。本质而言,民间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及不断革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