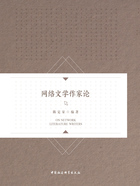
第二节 数字化生存与“棋盘效应”
数字化真的能像尼葛洛庞帝描述和预言的那样开创“无穷的可能性”吗?这些惊人之论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难免招致怀疑。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对尼氏的数字化生存学说提出了批评与质疑,但尼氏的自信与乐观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说:“我的乐观主义更主要地是来自数字化生存的 ‘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今天,信息高速公路也许还只是天花乱坠的宣传,但是,如果要描绘明天的话,它又太软弱无力了。数字化的未来将超越人们最大胆的预测。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并且发现,只有成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17]
他说自己的乐观不是由于发现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方法,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可行途径,乃至能造出清新空气和可饮用海水的零污染的机器人,这些毕竟都是梦想,就如天边的一片云,既有可能下雨,也有可能随风消散。“然而,数字化生存却完全不同。我们不必苦苦守候任何发明。它就在此时此地。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8]
从尼葛洛庞帝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所谓的“数字化生存”,从本质上讲,其实是“比特化生存”。由于对数字化的比特本质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加之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学者将“digital”译为“数字化”,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将其译为“数位化”,香港地区则常常译为“数码化”。中国三地学者对同一个词语的不同翻译,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大有深意。不同的译法,体现了人们对尼葛洛庞帝的“digital being”具有不同的理解。
由于尼葛洛庞帝以一个科普作家的通俗笔触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比特化生存的社会图景,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所谓的“比特之门”的开启者和掌门人理所当然就是尼葛洛庞帝本人,其实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误会。在这里,只要我们提及另一位“比特大师”的名字,这个误会就立刻能够得到纠正。这位大师就是微软公司掌门人比尔·盖茨。
对于大众来说,计算机普及之路的开创者是谁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比尔·盖茨等人的不断探索过程中,计算机及其延伸产品不仅被摆上了平常百姓家的书桌和窈窕淑女的梳妆台,而且进入了旅行者的行囊和中小学生的书包。当然,比尔·盖茨也只是千万个比特英雄的一个代表,但他无疑是开启“比特之门”的先锋队里一个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如今,“比特之门”不仅成了网络上的一个专有名词,而且也成了大众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扇堪称万能的百科全书式的智慧之门。
较早论及“比特之门”文化意义的李河在《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1997)一书中,对网络观念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进行了诗哲化探索。在这本网上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李河对比特与盖茨的名字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演绎,虽有过度阐释之嫌,却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风头人物、美国微软公司的缔造者——盖茨(Gates)这个名字“象征意味极强”。无论是巧合还是象征,比特这个数码精灵的成长一直与一位以“门”(Gates)为姓的比尔·盖茨的终身事业相关。在李河看来,这很像是一则意味深长的寓言。想一想 Gates 著名的 Windows (视窗)系统吧,我们还能找到比这些“门窗”更便捷的数字化生存之路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消费的具体情况而言,比尔·盖茨等人所研发的这些神奇的“门窗”及其相关数字化产品,如今已成了连接“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正是借助于这些通道,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才得以实现从“原子”到“比特”的跃迁。通道既然已经打开,世界必然为之改变。网络时代的文学,终结抑或新生?数字化生存是否必然要从本质上改写文学生存的意义?诸如此类的众多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关注文学生存状况的学者普遍的焦虑和惊喜,站在人类文明数字化生存的临界点上,人们迫切地想知道,穿越“比特之门”以后的文学世界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光景。
关于“比特之门”的说法,还有很多延伸的象征性的例子。譬如说,有人把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当作一个旅馆,那么“比特之门”就是通向这一旅馆的走廊。几乎所有房间的门都和它相通,旅馆的任何人出入自己的房间,都必须经过这条走廊。这原本是实用主义文献中被一再引用的实例,在这里,将“实用主义”替换成“比特之门”可能给人以突兀之感,但有意思的是,象征互联网的“比特之门”作为实用主义的产物,如今反倒把实用主义变成了自己的组成部分——“旅馆走廊”连接着的第n个房间。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化生存时代,互联网成了实用主义哲学最有说服力的万能工具。
众所周知,在信息传播媒介史上,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传奇故事。但无论是鸿雁往返的锦书相托,还是航空航海的邮件历险;不管是惊尘溅血的皇家马报,还是辐射全球的特快专递,所有关于信息传递及其相关媒介的故事与传说,似乎都难以与横空出世的现代数字化传媒产生的震撼与遐想相提并论。如前所述,许多人认为,代表数字传媒最高成就的互联网是冷战的产物,美国军方害怕敌军摧毁指挥中心,于是以网络形式实行多中心共存的天才想法促成了Internet的诞生。
笔者曾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法,直到有一天读了一则故事,竟然让自己对网络“冷战起源说”产生了怀疑。这个故事说,某单位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前一天,召集人突然发现通知书上的开会地点有误。于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625个与会者。但他发现,逐一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即便一次电话只需3分钟,连续通知625人最少也需要30多个小时。于是,他开始创建自己的“联络网”,首先只联络5人,被联络到的5人再分别联络5人,就是25人,重复一次就是125人,再重复一次就是625人,这比起单人逐一联系要快几十倍。
会议召集人是否受互联网的启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网络思维”绝非少数天才人物突发奇想的产物,它事实上是人类知识与智慧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此外,现代网络传媒的神通也绝非一个“快”字所能道尽其中的奥妙的。至少,我们在读完这个故事的同时,可能首先联想到的不是网络传播的奇速,而是数量的剧增。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古印度那个著名传说——“棋盘上的麦粒”。西萨·班·达依尔,这位国际象棋的发明人,他也许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但未必是一位称职的宰相,否则他绝不会对王国赏赐提出如此不知死活的荒谬要求。且不说在古时候,即便是今天,一般人都不会轻易相信如此出人意料的“怪事”——从“一粒麦子”开始的邀赏,竟然把一个炫耀恩德的国王逼上了绝路,不杀人则无法收场——据计算,全世界2000年生产出的麦子也抵不上宰相的这一“卑微要求”![19]棋格最初的增加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网络化”递进到一定程度,爆炸式激增的后果很快就会超出人们的想象。这种级数跃迁式的变化方式,使数字传媒乍一登场就产生了开天辟地般的惊颤效应。众所周知,数字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和众多先驱媒介一样,它原本只是作为工具手段出现的,但是,随着传媒及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工具的能量被一步步释放出来,微风起于青 之末,渐成天落狂飙之势,它以光辐射的速度横扫宇内,以核裂变的态势席卷八荒。其摧枯拉朽的力量捣毁了传统思维模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范围。
之末,渐成天落狂飙之势,它以光辐射的速度横扫宇内,以核裂变的态势席卷八荒。其摧枯拉朽的力量捣毁了传统思维模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范围。
于是,媒介的性质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从“参与生活、服务社会”到深度干预社会生活,从“人的延伸”渐变成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已不再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载体和中介,事实上它已演变为决定当代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些人甚至认为,现代传媒其实就是整体社会文化最为本质的存在方式之一。
中国学者惊呼,现代传媒正在改写生活,重铸历史。西方有学者宣称,现代传媒即将使人类重登巴别塔的千年梦幻成为现实。而数字传媒无孔不入的品性也的确正在大河改道般地刷新当代文化和日常生活。英国学者史帝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中甚至认为,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凭大众媒介来传达的。从古典的歌剧、音乐到诸如政客隐私类的庸俗故事,从好莱坞最新版本的流言蜚语到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时政新闻等,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的媒介所承载的信息,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的网络系统。
大众传媒以饱满的激情和公正无私的姿态老谋深算地参与社会生活,它们那些炫耀“友爱、关爱与博爱”以及“公开、公平与公正”的种种仪式都由一个名叫“市场”的幕后导演操纵。善于激发和网罗大众热情的媒介,无论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还是网络,貌似非功利的言行背后,都隐藏着某种不可违抗的利益原则,例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利益原则。说到底,只有造就市场“人气”的大众,才是媒介存在的最终理由。大众既是媒介服务的对象,也是媒介的信息来源;大众是客户,也是报道的主体。现代媒体的命运决定了它与大众的互相依赖的关系,并且一定是息息相关的。据此,史蒂文森等西方学者断言,大众传媒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无法再退还到以往的生活中去了。风头正劲的数字传媒的情况正是如此,只不过它使这一切变得如此强烈,就像微风拂水的细小波纹变成了倒海翻江的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