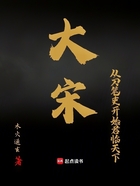
第21章 书惊门外客(下)
陈策看着一群小娃那期待的目光,便也化身成了一位说书先生。
“后来,那石猴从石中出世之时,目中两道金光更是直射斗府,惊的那天上玉皇大帝赶忙差遣千里眼,顺风耳前去查看……”
说来这古代娱乐项目确实匮乏,百姓们白天劳作,晚上造娃,几乎没有其它的娱乐方式。
这群由贫农组成的起义军,虽然攻下了杭州城,但内部许多的将官兵卒以及家中子女,还未见识过城中茶馆酒肆里的说书故事,自然也就无法抵挡听故事的诱惑。
院子里时不时的传来一阵惊呼,又时不时的响起一声哀叹。
“哇!那筋斗云竟比马还快……”
“那孙悟空的师父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山啊……”
“金箍棒竟这么厉害……”
就这样,站在院门前许久的韩三以及一名老道人久久才回过神来。
“此子竟有如此才华。”
老道人皱着眉头,半天才下了此结论。
一旁的韩三也是一副震惊的样子。
“沈道长,陈郎君刚刚讲的这是什么故事啊?还挺好听的。”
沈道长苦笑着摇了摇头:
“贫道也从未听闻,单单只是里面对天地构造的描述以及道家诸多经典的解读,不可谓不妙啊!
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还真是......妙啊!”
他称赞了一句后,随即抬头望天。
韩三疑惑的摇了摇头。
“沈道长你就别神乎了,一个山洞有啥妙的?”
沈老道瞪了他一眼,冷声道:
“你懂个什么?仅是这个名字就不是常人能够想出的,更何况其背后隐藏的智慧了。
贫道虽然师从天师府,但却无半点慧根,只能跟着师叔学些入世的医道。
但凭心而言,此子刚才讲的那些天地至理,宇宙宏观,无不与我道家诸多典籍不谋而合,甚至还有着独特见解别具一格。”
韩三虽听不懂沈老道叽里呱啦的说的一大堆东西。
但从对方那激动且赞赏的目光中不难看出,这院中的陈郎君定然很有才华,于是心里不由动起了念头:
“这么说来,那陈郎君很有学识?”
一旁的沈老道点了点头。
“还尚未可知,不过这故事若是出自他手,与我道家而言确实有些学识。
可知刚才他讲的那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为何吗?”
“俺刚才不说了嘛,一个山洞。”
“方寸之间是为人心啊,那孙悟空实则就是心的徒弟,学道就是修心。
还有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正对应佛家《楞严经》上说的人心有七十二像,极为善变,瞬息可七十二变。
那金箍棒更了不得,其重一万三千五百斤,也与那《黄帝八十一难经》上说的,人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息暗合。
其能大能小,能粗能细,可上天可入地,简直无时无刻不在说人心啊,此子……当真了得!”
“这,这么厉害?”
韩三张大了嘴巴,一脸的呆滞。
沈老道看了一眼呆愣的韩三,便一把推开了院门跨了进去。
———————————————————————
风撕鹅羽旋飞舞,一夜青山尽白头。
宣和三年正月初五,开封城里大雪纷飞。
在城西右相府邸的一处豪华暖阁中。
一名奴仆盖上鎏金香炉,袅袅紫烟便蒸腾而出。
身披金丝狐裘的中年人正卧坐在软榻边上品着热羹,他挥了挥手,那掌香的奴仆便低头退下,合上了毡帘。
此人,正是宣和元年一日连升八阶的特进当朝太宰,尚书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黼王将明。
他放下玉勺,伸出手。
一侧为其篦梳着长发的可人美婢,赶忙接过中年人手中的杯盏放至侧旁。
厅中的波斯裘毯上,七名绝美歌姬身穿半透的紫锦罗衫,半遮半掩间最是勾人。
特别是那摇曳间隐隐露出的玉足,恍若画中仙子入凡尘,简直美得不可方物。
“舞的不错,以后就这么穿。”
王黼颇为欣赏的赞叹了一句,便慵懒的躺在了美婢的腿上。
几名歌姬一听,便跳的更加大胆了起来,至于有多大胆,反正王黼已经沉迷在了其中。
“相公,有急报。”
仆人突然间的声音扰了王黼继续的雅兴。
“嗯?呈进来。”
王黼手指轻打着节拍,微微睁开眼睛淡淡的说了一句。
毡帘掀开,一名中年吏员低着脑袋不敢直视对方微微躬身呈上。
暖阁中的女婢接过吏员手中的黄纸札付交到了王黼手中。
王黼看到札付上封钤的朱红,不免露出一丝不耐烦,便直接撕开了腊封。
这才刚刚打开瞧上一眼,便猛然睁大了眼睛,他急忙坐起身子,眼中闪过一丝愠怒不过很快就被其压了下去。
他挥了挥手,众多歌姬美婢全都退了下去。
站在厅中不敢抬头的那名吏员,此时身子已经有些止不住的颤抖了。
“这札付经过几人之手?”
王黼问向厅中吏员。
那吏员赶忙回道:
“回,回相公,仅有下吏一人接手。”
王黼沉思了一下,将札付放在侧榻的桌上,淡淡开口:
“很好,去把报信的急脚驿卒抓起来,不得让任何人接触。”
“是,是。”
那吏人赶忙应下退了出去。
“来人!”
王黼对着帘外喊了一声。
顿时一位管家模样的男子躬身道:
“阿郎。”
“去将大理寺少卿请过来。”
吩咐下去后,中年人起身走至窗前。
吱呀一声,猛然推开了窗户。
冷风裹着雪粒灌进了暖阁,打在中年人的脸上,触感冰凉。
接着,他那刚被疏顺的长发被风扬起又乱了纹路。
他看向远处隐隐约约的宫闱,以及城中那处冒着尖角的艮岳,不由握了握拳头。
“那江南方腊不过疥癣之疾,真是一群无能草包!”
“杭州失陷……”
“知州弃逃……”
“哼!”
王黼嘴中自顾自的嘀咕着,仿佛外界的风雪再急,也吹不到暖阁中来。
没多时,毡帘外响起仆役的通报。
“阿郎,大理寺少卿祁少卿到了。”
“嗯。”
王黼轻嗯了一声,便见到毡帘掀开,进来一人。
来人四五十岁,一身的紫色官袍腰间垂着金鱼袋,幞头上还带着未化尽的飘雪。
“下官大理寺少卿祁彦昌见过王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