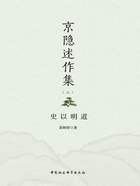
六 历史幽径和皱褶
历史幽径多,需要人的科学思维、理念去探研。历史常隐藏于文明的皱褶之处,需要人的明察、洞悉和鉴别。《晋书·戴若思传》引陆机《苦思书》名言:“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辩物。”此种潜伏、沉积于记忆深处的皱褶等待着人们理顺、发掘、回味和唤醒。那是一个个逝去生命的唤醒,再现其生机的可以检视个人与历史、思想与实践、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交往,审度人性的微妙、繁杂或诡谲。
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于多样之中,现实往往是理解历史的钥匙。细察世界那些挥舞铁拳的风云人物,究其内心深处的人性奥秘,可以帮助理解古人往事的某些奥秘。有时候,特殊年代的特殊行为,其苦难一角也可反映出美国作家海明威如同“冰山原理”中对人性的摧残图景,虽然这只是沧海之一粟。
历史上权力之争斗中,强权理论十分吊诡,这或许是历史自身的不幸。“竞争”中显现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疯狂工作,向对手笑脸相迎,无法使灵魂重返正常生活轨道。现代性不尽是美好的,它所追求的生命理念和引发的生命困境之间的悖论,令人触目惊心,其穿透力直指灵魂深处。历史学者应重视生命的精神内涵,用理论思维、审美和叙事力、兴趣、好奇心审视历史,对历史温度要把握住,善于在现代性冲击下坚守本真。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为何物?美与善有何关系?《孟子·尽心》有这样的回应:“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现代性有其花言巧语、矫揉造作的一面,它会用造作的文史势力组成新时尚虚空之美,把事物变成梦呓而失去本真。这是人类文明在转型时代、变革时代的悲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阿喀琉斯(古希腊神祇之一)能够与火药与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
然而,历史的镜子是明亮的,历史写作是一件真善美之事。苏轼说:“能者创世,智者述焉。”述什么?真善真美之后是诚信,所述者,立诚信为智者。现在有些重演马克思时代大不列颠的历史悲剧。史学家必须求真、扬善而爱美,只有诚信方能达到充实之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