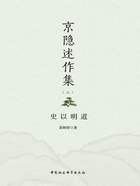
四 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大历史思维方式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自觉,源于大的历史思维方式的引导。
人类文明交往的广阔领域是时间、空间和人间,人始终是交往活动的主体。时间是历史的轨迹,空间是历史的坐标,人间是历史主体。人间的根基是物质的生产、再生产活动及其存在的社会关系。人类处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环境之中,其思维方式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思维路径,其特征思考的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个别事物的个别现象。
这个历史思维方式就是大历史思维方式。这里的所谓“大”,是宏观的,它不但表现在时间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也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在时间、空间和人间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交往活动过程之中。这里所说的“历史思维”同时也体现在辩证思维、创造思维、发展思维和互动思维等方面。这种思维就是唯物史观,其实质就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
我在人类文明交往的九条纲要中的第一条“人类文明交往的辩证互动规律”所说的“一个中轴线”,就是指文明交往的大历史思维方式是围绕着这个中轴线运行的。当然,这个大历史思维方式的运行路线是复杂的、曲折的,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的:“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辩证规律,就在于矛盾的统一性、斗争性以及统一和斗争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发展的。辩证发展,就是这种相互联系既彼此依存,又相互排斥而经过分、斗、和、合达成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的结果。这种交往互动本身就是矛盾与统一的辩证运动的结果。这种交往互动本身就是矛盾与统一的辩证运动进程,“是文明交往互动中两种思维方式的统一”[2]。
历史思维的特点是:①贯通古今中外纵横交织的思维能力;②言必有据的求真求实品质;③具有穿透力和厚重性的科学创造创新精神。自然科技和人文社科都有自身的历史,历史只有在积累沉淀中发展。任何科学思维都产生于其基本历史进程,历史思维就是辩证思想和哲学理论的思维。此种方式决定了研究工作的高度和深度。
人类史与自然史这种大的历史思维方式,在中外哲学史上都有表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表现“道”的生命力思维方式,反映一与多、道与物的辩证互动关系。在后期宋明理学家那里,把关学大师张载《西铭》思想核心归结为“理一分殊”,即认为存在的事物,是“理一”的有机统一整体,又是“分殊”的不同的具体表现,归根结底是“理一分殊”共同体。在“理一分殊”这个思维方式上,对“天”的解释,理解为虚拟的自然界,使系统完整观念变得不完整。[3]历史思维之所以成为“大历史思维方式”,就在于它的辩证性表现为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因而在研究和处理问题上能站在大自然与全人类和谐和解放的理论思维高度来思考文明史。理论思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处于文明发展的前列,实在是太重要了。把认识大自然置于全人类宏大视野交往之中,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人们的思维习惯,那将是文明交往自觉化之福。
文明史中包括自然史。上述对“天”的理解侧重社会而忽视自然的倾向,至今仍多有遗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哲学难道只和社会科学有关吗?前几年评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时,教育系统有人提出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结果不了了之。此事就说明了这种思维方式侧重于社会而忽视自然的倾向。人们不禁发问:难道自然技术不需要哲学吗?否则,人们怎么没有发现“哲学自然科学”的提法呢?实际上,文史哲的人文科学加上社会类的各种科学,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既有文科的基础学科,又有文科的应用学科,是比之“哲学社会科学”更切合实际一些。尤其与“自然技术工程科学”相对应,更显得合理。人们常简称为“人文社科”“自然科技”,与人类史和自然史两大科学相提并论,更可显示出大历史科学思维方式的科学性质。
事实上,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整体倾向于自然,可以称之为自然哲学家。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代表,直到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在总体上都是倾向于自然的哲学。这些著作的思想性、哲理性,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自然资源,其突出的特点是工具理性而与人文理性相互裨益、相得益彰。自然哲学的优点是分析的实验性和实证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其局限性自然是伴随成就而来的。关于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在《京隐述作集·哲以论道》中再深入探讨。这里仅就有关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大历史思维方式方面,谈谈自然和人类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说明二者在文明交往过程中的历史辩证性质。
实际上不仅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具有大历史的科学思维方式,只要思考自然科技的科学家,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有这方面体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生物系教授、生物地质与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童金男是古生物领域学者,他指出:“我的研究专业也是历史学。不过,我只研究人类出现之前的亿万年地球的历史。”他这个“历史视角”所观察的是地球和生物的演变史。由此历史出发,他最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他深有体会地说:“我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这就是站在全球、全人类,即从自然和人类交往的互动关系看问题,即从辩证唯物的关系上来看待文明交往问题。历史具有唯物性和辩证性的双重性质。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既关注自然科技,又关注人文社科,兼有自然和人类的互动与平衡联系,创立了唯物而又辩证的大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为“唯一”科学“大历史”观念,是对自然科技和人文社科这两大科学的综合概括,其本身就是历史的、辩证的、综合的创新思维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最初形成此种思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提自然史与人类史关系问题,后在出版时又删去这一段话,但这一大思路一直在进行。他们不只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改变了世界历史,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们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历史科学的宏观视野。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以自然界为存在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阶段历史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关于“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历史唯物论名言,也出自以自然史和人类史为存在根据而得出。列宁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大科学的两个方面。我在前面说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逝世是“历史科学”的损失,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再仔细研究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的各种笔记,其思考的仍是大历史科学理论思维方式问题。他们的科学研究历程就是从哲学出发,最后又回归历史,就是从大历史思维方式中获得自觉。
大哲学家培根说得对:“学史使人明智。”大科学家海森堡说得也正确:“在人类思想发展中,历史转折点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想方式的交会处。”“这种交会处”正是不同文明交往转折之地。他又说:“如果它们之间至少关联到这种程度,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到将来继之以新颖有趣的发展。”这种相互关联的自然与人类的交往密切关系,在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文明交往中必然会产生创新性的文明成果。“历史统一于多样,事物万变归常恒。分、斗、合、和均智慧,人文良知大化成。人类关注生产力,交往自觉共文明。”我在《老学日历·西东谣》中这三句可以作为本文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