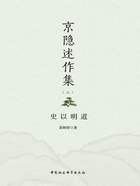
三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大视野
文化作为文明的核心,有其特殊意义,历来为历史研究者所重视。广义的文化,包括精神和物质方面,也与政治、经济、科技、自然方面相关,当然也同制度、生态方面相联系。然而,严格地区分,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社会思想和心理,以及价值观念等人类命运、生存精神状态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境界。人是具有高级思维的动物,文化不仅包括知识,而且包括具有对各种经历、经验的思考和升华,使之成为文明的结晶和成果。这就使文化成为文明的核心部分,也变成人类创造、创新定位的基点和思维活动中最值得开掘的价值所在。
文明包括文化,它的整体形态应该是精神、物质、制度和生态四个方面的统一整体。制度是文明的根本属性,它包括社会、政治文明,也体现着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同时还表现着人类生存、生活的时代风貌。生态文明更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其所蕴藏的人与自然的密切交往关系,日益凸显和加深。
精神、物质、制度、生态这四大方面的关系,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要方面。人类文明的生命在交往,而交往是环绕着这四个方面展开的。人类文明交往的价值在文明,缺乏文明价值的交往,对社会进步只能起负面作用。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灵魂,制度文明是根本,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与大自然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是文明与文化的异同,而是文明交往这个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问题。没有交往的文明化,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我理解的发展,就是人类交往的文明化,即人的现代化,这就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发展的主轴。人类文明交往是在冲突与和解,即在斗争与和解中发展的。“斗”与“和”都是文明交往中所表现的历史智慧。从历史的辩证法看,“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斗”并非目的。斗则进,进到何处?进到和解,才是目的。人类文明史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之间的三大交往,都是如此。人类文明史,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之间的斗争史,更是以共同发展、和谐共进的文明史。所谓“文明”,就是在这三大交往活动中,不断提高知物之明、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的文明交往自觉之明。显然,这“三知之明”不仅仅表现在文明之间的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每个文明之内的交往。当然,这种人类文明内外交往是互动的、互相作用的,这是世界历史普遍联系的辩证规律。认识和把握这种规律,关键在实践中寻找历史选择的相融点,把矛盾对立与统一规律中的一与多、同与异、常与变、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变运动,导向平衡状态方向运行。这就是“人而文之”的“文化”和“文而明之”的“文明”的人文精神真谛所在。
文明交往的历史大视野,是史以明“天人古今”之道。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指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的“际”,即事物之间的关系。司马迁还说过:“明天人分隔,通古今之义”(《史记·儒林传》),即是说,事物间交往有合适的界限和联系。司马迁在这里已经明白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交际关系要深入研究,古往今来的变化要贯通联系,个人研究要首创。这其实就是对知物之明、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的文明交往研究上自觉性的定位。学者的科学研究要关注这个定位,对人类文明交往史的贡献,应当是人们探求真善美的真正目的,而不是一味追求国内外各种奖项。当然,奖项是对研究成果的肯定,但决不是研究者追求的唯一定位。陈其泰教授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的观点,认为评价优秀的史著价值应当结合当时社会生活、民族心理、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从而揭示出其价值。这一从学术史理路上对“史学”与“文化”之间作互动参考,将研究成果定位于人类文明史上,也是跨学科的人类文明交往历史大视野的见解。
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1902年在《新史学》中说:西方引进的学科中,“为中国所国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这里以“最博大而最切要”来概括史学是对的,不足之处是详政事而略于文化。如果加上文化视角,那就更全面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则肯定了历史对文化的意义:“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特质是联系中的贯通性,首先是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贯通性,其次是空间上地缘的贯通性,更重要的是人间社会生活交往的变通性。此种变通性正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变化是史学时代性的大道,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的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互变正是历史科学所“明”之大道。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这种大道有所体悟。他说:“自登朝来,年龄渐长,阅历渐多。每与人言,多言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里的“每读书史,多求理道”的“理道”,正是“史以明道”的“道”。这也就是清代大学者龚自珍所留下的治学名言:“欲知大道,必先明史。”文以载道,史以明道,正是诗文为时为事而著作,不为单纯地为文史而著作。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他自己把其中要旨表述得很清楚,即“五为”与“一不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观察人世,他的作品,“篇无定论,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这就是他的历史经验中的闪光之点:“每与人言,多询时务”,即对时代发问的问题意识;“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即在学习历史中寻觅规律性之大道。实际上,唯物史观的“史”,本身就包括了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观察世界的历史观念。
众所周知,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有“回归历史,获得自觉”的名言。他从哲学史角度讲,哲学回归历史,才能真正获得自觉。黑格尔还有句名言:“哲学史是哲学的总结,哲学是哲学史的展开。”哲学史和哲学这种辩证互动交往关系,我将在《京隐述作集·哲以论道》中详谈。这里只是要说明历史科学的自觉是人类根本的自觉这个哲理。人类文明交往的大视野,正是我们观察自然、人类和人的自我身心三者交往联系性与贯通性的广阔视野。这也就是恩格斯为什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演》中说马克思逝世是“历史科学”损失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正是唯物而又辩证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黑格尔的“回归历史获得自觉”的人类交往文明化自觉,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它让我对历史自觉是人类根本的文明自觉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