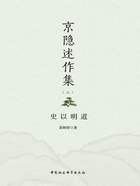
九 身体史(人体史)
英国史学家罗宾·奥斯邦在2011年出版的《古典希腊身体的历史书写》(History written on the classical Greek body),是一本将文献资料和人体图像相结合起来研究的古希腊史著作。严格地说,身体应译为“人体”,是人体图像的历史研究。作者的研究历史方法是把文献的历史书写与人体的图像史书写互相结合的写作路径。这很类似我国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路径,不同的只是把此种方法细化到人体历史上。这与希腊的艺术特征有关。各古国史中,都有人体艺术,但古希腊特别发达,反映了古希腊文明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史、艺术史和考古史中的人身史,是建立在可视资料基础上生动的历史书写。
在罗宾·奥斯邦看来,历史中的文字图像元素,与文字语言并不相同,它是与文字图像的符号结构以不同方式构建起来的。完整的历史,必须建立在这两种不同方式认知的基础上,方能全面把握。他强调人体史应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之中。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看来,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社会史新史学到7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新史学转变的趋势来看,人体史是以社会文化考察为研究对象的学派。尤其是古典人体史就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史中的妇女史研究,也追溯到古希腊罗马这个历史源头上。这是文化、文明史研究的必然回归,因为,人始终是历史——尤其是文化、文明史——核心,是文化、文明史的主体,是人类史、自然史互动文明交往的最积极、主动和积极创造性要素。
身体为人的外形组合、总称为人体。另有一说称:身体为人头以外躯干,即颈以下、大腿以上的部分;也有广义的、包括头脚在内的躯体;当然,还有身心之说,把身体与心灵相对应。屈原《九歌·国殇》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之句,把身与神灵魂魄鬼雄联系在一起。人的身心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深层部分,骨肉与心灵是身心感知交往过程。坦荡的心胸与常戚的情绪,物我虽殊异理本相同。人与自然、人与人都要通过人的自我身心去体味、去体验、去力行,方能致用。中华文明中,儒家讲“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讲“修之身”“修之家”“修之天下”,都强调处理好身心和谐交往的意义。这里有几则关于身躯问题的说法,存以备考:①《孟子·尽心》:“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身躯而已矣。”②《晋书·刘曜载记·陇上歌》:“陇上壮士有陈安,身躯虽小腹中宽。”③杜甫:《送韦十六》诗:“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80年代,文明与人类身心关系引起学术界关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有《疯癫与文明》《性史》等著作,分析了身体与权力之间的交往关系。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规训、塑造作用,进入了思考分析范围。这对古典时代西方身体史的深入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思潮中,社会性别、文化特征,跨学科、多方法,以及语言、文学、医学、艺术、考古方面的成果,也促进了身体史的研究。
由此,我想到中国古典身体美学与英美身体美学的区别。在中国,人们的农耕体验实质上是身体的体验。这一体验特色是把顺应身体作为最高的智慧。《道德经》把身体作为哲学思考的起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儒家也把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尔雅·释诂》则把身视作“我”的代词:“身,我也。”由身体出发,又回归身体,人的视、听、嗅、味、触这“五觉”进入了从物象、情象、意象、意境进入境界身心交往过程。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历史是人类和国家的传记,其中包括着人类自我身心交往这基础性的文明关系。文字记录和图像表述,这两条人类历史写作路径理应相通互补,也是人类自然史中研究的两翼,其深层关系是人的身心交往互动关系。身心交往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复杂深奥问题,自知之明在这里显示着自己的局限性。
由此,我又想起英国另一位科学家比尔·布莱森写的《人体简史》。了解人体科学,让我们体悟人生的历史哲学。对人体的认知历史,最终都会回归到自我。比尔·布莱森在《人体简史》中解答了“制造一个人需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根据2013年剑桥科学节上皇家化学学会的计算,构建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他有着人类的典型体格)必需的所有元素需要96546.79英镑。但是没有谁能用元素造出一个人来。元素有价,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据《人体简史》统计,普通墓地的拜祭时间为15年,此后就从他人记忆中消失了。人活着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身心健康,“充实地活着的时候,一切挺好,不是吗?”比尔·布莱森这句话真是正确,因为死去是迅速的、永远的。知人体历史,增人生智慧,信哉!